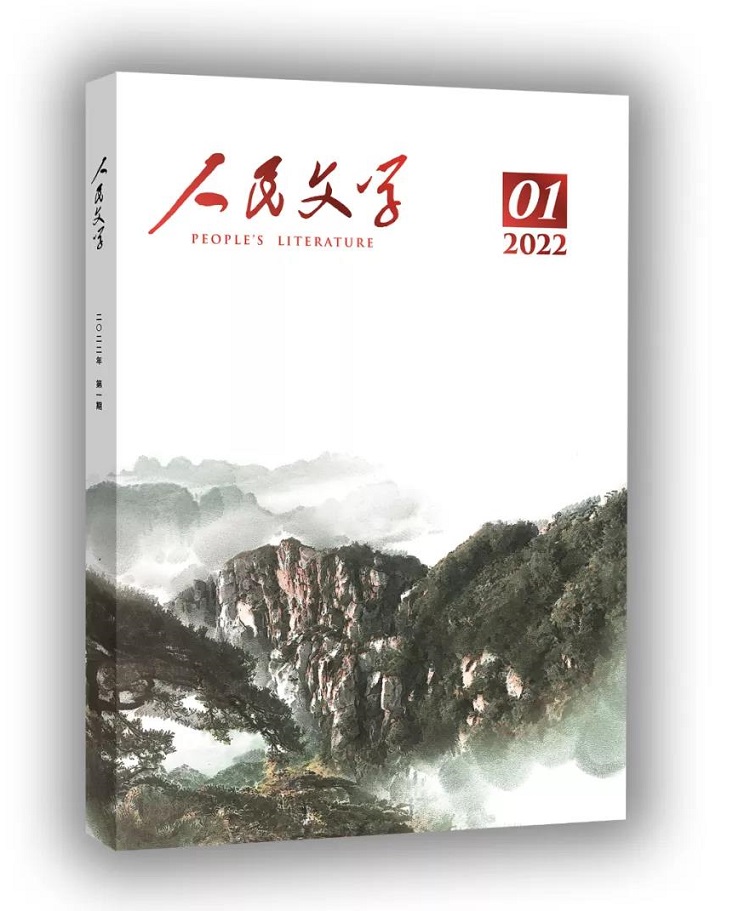
1、大金子
一场急雨。
晴空中飘来一团如山的乌云,乌云从上端坍塌下来时,其中蓄积的能量就弄得山谷中雷鸣电闪。
西面山上的栎树林、石崖、石崖上悬挂的飞瀑都还被太阳照着,山峰后的天空也还一片湛蓝,谷中的露天金矿上却雨脚如注。一道道闪电蜿蜒而下,雷声贴地滚动,它们在寻找铜和铁。闪电和雷找到了铜,牛脖子上的铜铎,一团蓝色火焰在牛肩胛下蹿起,长毛纷披的畜牲倒地抽搐。闪电和雷找到了铁,木板屋顶上的电台天线。电流顺着天线蜿蜒,像咝咝叫着的大蛇,进入木屋中,电台噼噼啪啪爆出蓝色火花。报务员摘下耳机:“电台烧了。”
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乌云中的能量耗尽了。雨水落尽,雷声隆隆远去。太阳照亮湿淋淋的草木,和山坡上能住上千人的座座木屋。空气充满了硝石刺鼻的味道。敛声的鸟突然开始鸣叫。河滩上站着许多湿淋淋的人,他们是淘金的金伕,还有哨位上持枪的哨兵。急雨造成的浑浊洪水在他们眼前急急流淌。
等到穿着干衣服的哨兵来换了岗,被暴雨湿透的金伕子才被允许离开现场。
金伕子和下岗的哨兵一起鱼贯进入金矿出口处的木屋,在一间屋子里脱光湿衣裳,再在另一间屋子里换上干衣裳。两个股长目光炯炯监督整个过程,换衣服的金伕子要在他们面前脱下草鞋。脱下的草鞋扔在一个大木桶里,装满了,用橡皮水管淘洗,几百双草鞋能淘出几两金子来。脱了鞋的金伕子还要在两个股长面前张开脚趾,张开嘴,以防夹带。这是一座富矿,整个流程都是为了防备有人夹带了金子走出矿场。要是有人能夹带出一片麸金,价值起码超过好几天的工钱。
这也是急雨到时,他们必须待在原地不准离开的原因。
金伕子吴树林在股长面前张开左脚趾,又张开右脚趾,忍不住说:“股长,怕是要出大金子了。”
大金子,俗名狗头金,是重达几斤几十斤的天然金块。金矿开挖这一年多,已经出了五块大金子。
股长说:“出大金子好啊,有利大后方建设,有利抗战。但你咋个晓得?”
吴树林说:“这么急的雨,肯定是雷闻到了味道,找大金子来了。”
股长笑笑:“喝姜汤去吧。雷没有找到大金子,反倒把电台打坏了。”
哨兵赵兴旺用干毛巾擦拭淋湿的步枪,要在股长面前脱鞋。
股长说:“你站哨在坡上,又没下到矿里,不用脱了。”
赵兴旺说:“又要出大金子了。”
“雷真是来找大金子的吗?”
“我看反正要出大金子了。”
急雨到来之前,他站在坡上的哨位,看河沙被金伕们一筐筐挖起来,倒进淘金的木槽,那些被水冲激的沙中有比往天更多的金粒在闪光。他还看到,金伕子吴树林端起一筐沉重的沙,身子一歪,差点儿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上滑倒。金伕子打滑的脚,蹭去石上的青苔,闪出了一团金光。赵兴旺不晓得吴树林的名字。只看到他端起那筐河沙,看到脚下那团金色时,机警地看了看四周,就故意让抱着的筐脱手,让倾倒出的沙把那团金色掩住了。赵兴旺差点儿喊出声来:“出大金子了!”
恰好这时,闪电像鞭子一样抽在树上,雷声炸响,然后,如注的急雨就下来了。
赵兴旺站在雨中一动不动紧盯着溪上。几次,雨帘遮住了视线,当那个金伕子的身影显现出来时,他还站在原来的地方。赵兴旺看见他还仰起头来,任鞭子一样的雨线抽在自己脸上。赵兴旺想,这家伙一定想发出狂笑,就像自己也想仰脸在雨中狂笑。
雨停了,太阳出来。哨声响起,浑身湿透的金伕子和哨兵们往换衣换鞋的木屋移动。
赵兴旺问那个金伕子:“你叫啥子名字?”
“我叫吴树林。”
“我记住了,你叫吴树林。”
“你站你的哨,我挖我的金,记我名字干什么?”
“记住了,就不怕你跑掉。”
刚才在急雨中,两个人都只在心里狂笑,此时都有点儿多话了。
脱湿衣服的时候,吴树林龇牙咧嘴,刚才在溪中假装失手,把那筐揭出了大金子的沙倒回原处时,把腰闪了。吴树林和赵兴旺,两个人光着身子在股长面前过,两个人都有些多话,都对股长说:“要出大金子了。”
赵兴旺要像金伕子一样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股长对他说:“站在坡上的哨兵不用脱鞋。”
哨兵不光是站在坡上,沾不到金沙,脚上穿的也不是草鞋。护矿的哨兵穿的是帆布帮橡胶底的鞋,就是下到溪里,也沾不上沙里的碎金子。
在另一间屋子,大家把身子擦干,彼此的身体袒露无遗。吴树林身体强壮,腿上胳膊上肌腱突起。赵兴旺却盯着吴树林双腿之间:“本钱不小。老家的女人不知怎么念想。”
吴树林说:“老子挣够了钱回去,叫她……我还可以帮忙去照顾你家婆娘。”
赵兴旺一边穿上干衣服,一边说:“老子当兵吃粮,没有安家,人家的婆娘都是我的婆娘!”
旁边有人笑道:“看这两个过嘴瘾的!可惜这山上只有牦牛是母的!”
大家出了屋子,穿过一片草地,到食堂去喝暖气祛寒的姜汤。
换班的金伕子和哨兵进了金矿。
喝姜汤的赵兴旺和吴树林都捧着碗从木屋里出来,站在坡上,眼睛都望着刚才现出了一团金光的地方。
吴树林看一眼赵兴旺:“啥子都叫你龟儿子看见了!”
“上山打猎,见人有份。那么大份财喜,一个人独吞谨防屙不出来!”
这时,就听到溪水中淘沙的金伕发一声喊:“出大金子了!”
听这一声喊,吴树林和赵兴旺都腿发软,心发空,身子摇晃。
急雨造成了一场局部的小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急流冲去了溪上的沙子,确实就有大金子露出来了。一时间,见了金子的人、没见金子的人都在喊:“出大金子了!出大金子了!”
所有人都往出金子的溪流处奔跑。轮班的金伕、不在哨位上的士兵、警卫连长和矿长都向着溪边奔跑。
只有赵兴旺和吴树林站在坡上不动。
吴树林身体摇摇晃晃,他这是快晕过去了。
赵兴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对吴树林说:“财喜,枉然!枉然了。”
吴树林却站稳了身体,低叫一声:“不是那个地方!你看嘛,不是那个地方!”
赵兴旺站起身来,果然出了大金子的不是吴树林发现大金子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洪水非但没有退去,还在把别处的沙子冲来,在那里沉淀。
大金子出水了,被搬上了岸。
哨兵拉动枪栓,警告金伕们不准走出矿床。大金子起上岸,把头立即用一块红绸布把它盖住,放在淘金的水车上。把头和发现它的金伕对着大金子磕头,按规矩,该杀一只大红公鸡,可这山上没有。只好当场宰了一只羊,又放了一挂鞭炮,矿长给淘出大金子的两个金伕子各赏了五个大洋。这才由两个士兵把蒙着红绸的大金子抬着,往金矿上唯一的那座两层楼的木屋去了。
揭开红绸,大家眼中都露出崇敬的目光。金块表面凸凹有致,棱角早已经在溪流中打磨光滑。像一朵生根在山头的云,也像一朵长在老树上的灵芝。
财务股长说:“就叫千年灵芝?”
矿长摇头:“俗了,俗了。还是叫出岫之云吧。”
“矿长到底是当过参谋长的,肚子里墨水多。”
矿长说:“少说屁话,拿秤来。”
大金子称重七斤三两。矿长把大金子用红绸包起来,锁进保险柜:“发报,向刘军长报喜!”
报务员向他报告:“火闪和雷顺着天线钻进来,把发报机烧坏了。”
矿长说:“我看你这个发报员一对吊梢眉毛,日霉得很。”
矿长又叫值班员拿矿务日志来:“我说,你记!”
矿务日志上便有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五十七分,雷暴雨后,国营哈克里金矿出狗头金一块,全重七斤三两。该金出水,金伕子祭礼时,本矿上出现彩虹一道,此乃天降祥瑞,只可惜因电台被雷电损坏,不能及时报刘军长知道。”
2、法王
山上寺庙的法王带着一众喇嘛出了寺庙下山来了。
寺院在山腰,有六百六十名僧众,背靠一面长满松树的岩石山峰,占地广大。
传说寺庙所以选址在此,一说是因为第一世法王,一个游方高僧行脚到此时,壁立的岩石上有天生菩萨像示现。二说,寺院建此就是为了守护谷中旺盛的金脉。寺庙遥对着终年积雪的无量山顶峰,溪流从北面冰川发源,水绕山环百余里地,飞珠溅玉冲出南面峡口,在寺庙下方平坦开敞的山谷中平静下来,曲折蜿蜒。不是如此地形,湍急水流从山上岩石中冲刷出来的金子不会在这里积聚沉淀。
眼下这位高大肥胖的喇嘛,已经是这寺庙的十八代法王了。
寺庙志记载,哈克里大寺建成以来的两百多年间,寺院一共只在金矿里取过十八次金子。第一次,是建寺时为殿中佛像装饰金身金面。以后十七次,取得更少,只是为往生的十七代法王装饰金身。法王往生后,遗留在尘世的肉身以秘传法制成干尸,涂金后,盘坐肉身塔中,有序排列在殿上享受香火,接受供养。
民国初创,川军进入,不顾寺院反对,开采金矿。
本代法王常在夜深人静时,在前十七代法王的灵塔前伤心倾诉,因为在他任上没有守护住金矿:“末法时代来临,金脉被掘断,神山的宝藏被掏空,地方的财气将要枯竭,我哈克里政教福地衰败的日子已经可以看见了。”
最近,矿上连出大金子的消息更让法王伤心欲绝。
今天,矿上又出了大金子的消息,随着矿上响起的鞭炮声,闪电一般传遍四方。
法王再也坐不住,率领着一众武装喇嘛,下山往矿上来了。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他要请求矿长把大金子埋回地下。他们可以采走那些麦麸皮一样的、沙粒一样的细碎金子,但不能把那些大金子都挖尽了。那是山神的五脏六腑,任谁也不能让山神的肚子变得空空荡荡。
但矿长对他的出现视而不见。
股长向矿长报告:“刘参谋长,法王下山来了。”
刘矿长说:“我现在是矿长,不要再叫我参谋长了。”
刘矿长以前是川军某部的团参谋长,抗战爆发,随川军上了前线,保卫大武汉战役中负伤,现在领两连兵警卫金矿,并兼任矿长。
刘矿长说:“庙上不是在夏安居吗?他们不是怕这些日子出行,会踩死很多虫子吗?”
股长说:“要不要搭个帐篷,请法王喝个茶?”
“你龟儿子要是想改行开茶馆,递辞呈来我批,还送你一顶帐篷。”
股长就不再说什么了。
刘矿长说:“我不是舍不得茶,我是不想看法王伤心欲绝的模样,我不想再听他请求把大金子塞回到山神的肚子里去。他想看就让他看,叫哨兵不要拦他!”
法王进到矿上,看见出大金子的河滩上放过鞭炮的一地红纸屑,和金伕们祭过他们的邪神后留下一摊变黑的羊血。法王就晓得,真的是又出了大金子了。他带着悲伤的神情在矿区四处徘徊。和往回不一样,刘矿长没有出来迎接,几个股长也没有一个出来迎接。只有站在山坡上一个个持枪的哨兵,漠然而警惕地注视着他们。
“啊哈!”这是法王喟叹金矿上的人没有礼貌。
“啊哈哈!”这是喟叹金矿上的人不是一般的没有礼貌。不顾他的悲伤,也不顾他为悲伤而口干舌燥。
最后,还是庙里牵了马下来,让他骑上马回庙里去了。
回到庙里,法王一言不发,听几个管事的喇嘛在底下商量:“他们挖出了大金子,我们要把每条山路都看守起来,不让他们运走!”
这样的议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矿上每次运金子走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路上伏下暗哨,监视,追踪,但都没有结果。因为押运金子时,矿上都会派出一整个连队,几十支步枪,十几支汤姆冲锋枪,和两三挺轻机枪武装护送。还有军部派出的部队半道接应。庙里的咒术师会念动咒语,用鸽子蛋大小的冰雹袭击他们。但是,他们都头戴钢盔,冰雹砸在钢盔上,非但不能伤到他们,反而自己立刻就粉身碎骨了。
但他们仍然一次又一次重复策划跟踪和伏击。
喇嘛们还私下怪罪法王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出任了川滇边第四绥靖区区长。法王做晚课的时候,寺院的襄佐来向他请求用绥靖区区长的官印。
法王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能让他们把大金子运走,寺院人手不够,要向各村寨下令,征发乡丁。”
襄佐说:“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为做而做,会有什么用,但你们爱做就去做吧。”
“我也是为了法王的权威,要是什么都不做,一直都束手无策,法王就要失去僧众和百姓的崇信了。”
法王拿出大印,叹口气:“拿去。”
他想说,出动了庙上的喇嘛兵,征集了四乡百姓中的火枪手,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大金子细金子被运往省城,不是更要叫僧众和百姓看轻自己吗?但他没有说。他只是叹着气,执了壶,转到后殿,在一座座肉身塔前,往一盏盏供灯里添上灯油。
塔里,敷了金,盘腿坐着的都是他的前世。他虽然体态松弛臃肿,却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干枯一样,发干发紧。
3、吴树林
入夜了。
吴树林从金伕们的通铺上起来,把头警觉:“起来干什么?”
他说:“拉屎。”
他出去,把盘在身上的绳索藏在茅房里。
这是前半夜,还有金伕子借着月光在矿床上工作。
下半夜,月亮下去了。金矿上沉寂下来。通铺上鼾声四起。吴树林再次起身。这次,他已经穿戴停当了。山上冷,他把平常当枕头的军棉衣也穿在了身上。棉衣夹层里,还缝着这一年多的工钱,两沓子纸钞。
他从茅房取了绳索,绕过哨兵,来到溪边的时候,乌云把星光也掩去了。四周变得一片黑暗。赵兴旺的脸还是朦胧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是一团模糊的白。他用步枪捅捅吴树林:“嗨!”
两个人摸索着下到水里,轻轻移步,不让水发出流淌以外的声响。
白天,吴树林把那一大坨金子周围的沙都掏空了。流水又带来了一些新的沙子,不多,几下就掏尽了。当吴树林把那坨大金子用绳子缠绕好,就已经被夜半的溪水冷得浑身战抖了。赵兴旺往他口中塞了一条干辣椒,又灌了一口酒。把步枪穿过绳套,自己肩着枪托这端,那一端让吴树林肩着。两个人半蹲在水中,同时低声说:“起!”
大金子松动了。
再说一声:“起!”
大金子就起来了。
两个人把金子抬过溪流,抬过一片沼泽,进到了对岸密密的栎树林中。他们脚不停步,一直顺着缓坡向上抬了两三里地才停下。这时,东边参差的山峰上面,启明星已经升起来了。吴树林要继续走。赵兴旺不同意:“走不远的,回去,晚上再走。”
吴树林还是要继续走。赵兴旺把枪顶在他胸口,拉开栓:“老子回去,准备些吃的。你龟儿子要走就走,我看你走得到多远。”
吴树林说:“你说这金子有多少斤?”
赵兴旺收了枪,揉着肩说:“怕是有五六十斤。反正比以前出的都大。”
“这才是真正的大金子!”
“兄弟伙,这么大个宝贝,真要盘出山去,着不得急。”
吴树林就和他回去。天亮前,两个人都潜回矿上,回到床上睡觉,直到早上,才和大家一起起来,洗脸吃饭。赵兴旺还和警卫连一起出了早操。
白天,吴树林和同一班的金伕子下到溪水里,他故意站到昨晚出大金子的地方,脚下是刚填上新沙子的空洞,心里却充满了幸福。幸福感只有靠不断去看站在哨位上的赵兴旺来分享。赵兴旺比他冷静,吴树林看他的时候,他就用目光去望山上那些通往外界的小路。那也是引导吴树林观察,让他看见那些小路上有神秘的人影出没。
赵兴旺大声对巡哨的连长说:“肯定是出大金子的消息走漏了,庙上的人把每条小路都看起来了!”
连长拍拍腰上的枪:“那有个毬用!这家伙又不是吃素的!”
赵兴旺心里也充满幸福感,要用什么方式表现一下:“连长把你的枪借我使使,我去把那些鬼人干翻几个!”
连长翻翻眼:“你他妈敢跟老子这样说话?!”
“连长不要怪罪我,等发了饷我请你喝酒!”
“咋个那么多屁话,给老子把眼睛盯紧出金子的地方!”
一个下午,吴树林都盯着小路上那些时隐时现的人影发愁。换了岗的赵兴旺却去矿上供应部买了两个牛肉罐头、一包点心、半斤水果糖和一瓶白酒。人家没有问他,是他自己说:“我要请连长喝酒。”
军需股长翻翻眼睛:“管毬你和谁喝,钱!”
“记在账上,从下月饷钱里扣。”
“不打仗,没有战功,一个平头大兵,靠站哨能有几个钱!”
“股长行个方便,再赊两盒香烟、一盒火柴。”
晚上,月亮出来得晚,下去得也晚。
月亮下去后,吴树林才听到猫头鹰叫声响起。他起身,出门时,将把头脱在床前的胶底军鞋掖在了腰上。两个人摸进树林,找到了用栎树枯叶掩藏起来的金子。吴树林很固执,一定要给大金子烧一炷香。
赵兴旺说:“你不怕火光暴露了目标?”
吴树林说:“满山都是鬼火,锤子个暴露目标。”
确实,树林中到处都有腐朽的树木冒着星星点点的磷火。吴树林点了香,竖在大金子面前,还跪下去磕了头:“大金子爷爷,要劳动您启驾了啊!”
他还把脚上的草鞋换成了顺来的胶底军鞋,赵兴旺挎包里塞着吃的东西,身上缠着子弹带,便把腰上四枚手榴弹取下来,捆在吴树林身上。这才把步枪穿过绳套,说声:“起!”
两个人摇摇晃晃抬着金子在栎树林中穿行。
就这样一直摸索着走了两里地,才出了树林,来到朝着西北方向的路上。
赵兴旺低声笑道:“应该绕过那些龟儿子的暗哨了。”
吴树林把枪换了肩:“你说这坨金子有多少斤?”
赵兴旺说:“等出手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
路上,两个人走得轻快多了。
吴树林说:“老子第一次穿胶鞋走路!”
赵兴旺说:“乡巴佬!老子当兵三年,都穿过十几双了!”
就这样,两个人一直走到天亮,翻过两座小山头,面前耸立起一座更高的山峰,才进入一片有溪水的树林,躲藏起来。
一进树林,吴树林就趴在地上喝水。
赵兴旺小心,回到路边,把他们进入树林的脚印都清理干净,还撒上了好多枯叶,才反身回来,抽出一支烟,掏出火柴要点,又把烟插回盒子里:“不能叫味道飘到路上。”
吴树林在看金子。太阳升起来,金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拿块木片想刮去金块表面的泥沙和青苔。赵兴旺阻止了他:“瓜娃子,怕别人看不见,非得要宝贝放出光来!”
“它长得多漂亮啊!”
大金子确实漂亮。立在地上,上小下大,表面光滑,像一枚仙桃。
吴树林面孔涨红,眼睛放光:“班长,你说值多少钱!”
赵兴旺不是班长。金矿上也有等级。金伕子们叫任何一个哨兵都是班长。
“反正讨三房老婆、买几十亩地都有富余!”
“三个老婆!几十亩地!”
清晨,第五棚的金伕子把头起床,伸脚在床下找不到鞋,弯腰看,一地草鞋,独不见了自己那双胶底军鞋。这才发现,棚中还少了一个金伕子吴树林。
军号响起,警卫连队集合点名。二连五班赵兴旺也不见了。人不见了,枪弹也一起不见了。
又一个消息闪电般传开:真的出大金子了!姓吴的、姓赵的两个龟儿子带着大金子跑了!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吴树林老站在溪流里一个地方,老看站哨的赵兴旺和对岸的树林。闷头闷脑的赵兴旺老跟人搭话,下了哨还去供应部赊账买了吃的东西。
一天搜索。发现了踪迹。
地上的脚印很深,说明两个人真的抬了沉重的东西。
脚印一路到了栎树林里。还找到了掩藏过金子的地方。是那么大的一个坑啊,那是多重的一块大金子才压得出来的啊!
还他妈烧了香!
还他妈扔了一双破草鞋!
追踪,那么明显的脚印踩在夏天的松土上,踩在枯枝败叶上,他妈的太好追踪了。他们肯定不敢跑到路上去!结果,这两个挨刀的真的就跑到路上去了。绕过庙里派出来监视的暗哨跑到路上去了。一到人马来来往往的路上,就失去他们的踪迹了。
追兵们都茫然地看着刘矿长。
刘矿长说:“要是你们,大白天敢抬那么大一坨金子走在路上?”
“不敢!”
“那算算他们走到天亮能走到哪里!”
马上就有人奉承刘矿长英明。
刘矿长说:“把这地方封锁起来,我叫这两个龟儿子插翅难逃!
4、赵兴旺
吴树林和赵兴旺在大金子旁,靠着株大柏树睡着了。
追兵的动静把赵兴旺惊醒了。
看身旁的吴树林脸上幸福的表情,肯定是在梦中做置地娶老婆的事情。赵兴旺捅醒了他。听到路上的动静,吴树林脸上的幸福表情变换成了惊恐。
赵兴旺持枪对着下方,示意他刨坑。他刨去落叶,刨去黑土,露出下面纵横的树根。用刀斩去这些树根,大金子自己一歪身子,倒进了坑里。大金子被黑土和腐败的落叶掩去。赵兴旺叫吴树林和自己一起离开。
吴树林舍不得:“班长,不要金子了吗?”
“只是不想和金子死在一起。”
然后,他往山上爬。吴树林也跟了上来。
在几块岩石后面,赵兴旺停下,找到一个可以用枪瞄准掩藏大金子的地方:“老子要叫想得大金子的人死在它跟前。”
听得到下面路上,那些追兵咋咋呼呼地来来往往。
吴树林很担心:“班长,我们走不出去了吗?”
“听我的兴许就走得出去。”
“兴许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走得出去吗?”
赵兴旺咬着牙说:“兴许是什么意思?就是赌一把。只赌一把。赌的是命。”
“我害怕。”
“那你下山去自首吧。”
“那我就没有金子了。”
“那就不要害怕。”
“班长不害怕我就不害怕。”
“老子成了你龟儿的主心骨了。”
隔一会儿,吴树林又说:“看样子晚上也走不成啊!”
“也可能永远都走不成。你去自首吧。不过,你真要去,老子从后面一枪就把你崩了。”
吴树林说:“我饿了。”
“你不要打老子包里东西的主意,山里饿不死人,没事干就去找点儿吃的东西。”
吴树林看着树上歇着两只松鸡,带着哭腔说:“也不能开枪打下来呀。”
“不能生火,你也不能带毛生吃吧。”
赵兴旺看见几棵正在结蕾的野百合,他把地下的鳞茎挖出来,这是可以生吃的东西。虽然因为植株将要开花,那些鳞茎都有些空瘪了。到底还是有些淀粉,还带着水分和甜味。
这是第一个白天。
晚上,他们把金子起出来,潜行了不到五里地,又照前一天的方式潜入了树林。
白天,那些追兵看到山上有野羊和鹿出现就乒乒乓乓胡乱开枪。两个人从藏身处看见中枪的野羊从山崖上滚落下来。看到烧野火的青烟升起来,还闻到了烧烤野羊的肉香。
赵兴旺说:“但愿他们给我们剩下一些。”
吴树林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世上总会有日怪的事情。不相信世界上有日怪的事情,你就不该打大金子的主意。”
“这么大坨金子,怎么让人心头不热。”
闻着山下飘上来的野羊肉香,两个人生啃了些长老的箭竹笋,又在林间睡了过去。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赵兴旺带着吴树林横过山腰,往回走了好几里地,在一座小山头上停下来,赵兴旺叫吴树林捡干柴准备生一堆火。
吴树林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动手。
赵兴旺说:“老子背着枪,比你累。”
吴树林就捡来干柴架了个火堆。赵兴旺爬到树上,把路上追兵停留的位置看清楚了。
黄昏时分,赵兴旺把火点燃,又在火上压了些湿树枝。为的是让火堆闷烧,只冒烟而不发出火光。两人迅速往藏着金子的地方走,回头见追兵们分成几路朝着山上冒青烟的地方包围上去了。
两个人抬着金子来到路上,天已经黑了。赵兴旺把一颗手榴弹打开盖子拿在手上。他们来到了追兵们生火的地方。火堆边真有没吃完的野羊肉。两个人停下来,把那些东西都吃干净了。身上有了力气,脚步就轻快多了。没走出三里路,他们又遇到另一个追兵们生火烤野羊的地方。那里剩有更多的肉。他们拿了肉没有停留,这样一直走到月亮快升起来的时候。
吴树林说:“该藏起来了。”
赵兴旺催他加快脚步:“你狗日的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吗?”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直到月亮真的升起来,把四周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本来,他们要出山,该是往东,路却顺着山势往西而去。月亮从背后升起来,吴树林看见自己长长的身影在自己的前面,滑过路边的岩石、树丛,心里越来越害怕。害怕了腿就软,他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赵兴旺警告他:“走稳!走稳!你他妈要是跌伤了,老子只好把你杀了!”
吴树林更害怕了。他这才意识到,在这荒山野岭中,赵兴旺有枪,为了这坨大金子完全可以在背后开枪。想到这个吴树林就更加害怕,腿更软,走得更加跌跌撞撞。再走一阵,他居然把心里的害怕说出来了:“班长,你狗日的不会黑吃黑吧?”
赵兴旺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这么大坨金子我一个也背不动。”
“你发誓!”
“发你妈啥子誓,快走!”
就这个样子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一直走,一直走。小路汇入了大路。这是走到真正的大路上了。再一直走,一直走,直到大路分岔出一条小路的路口才停下。吴树林脸上挂满了汗水。赵兴旺站在路口,他要做一个选择,往大路走还是走小路。最后,他选择了大路,但他布了疑阵,他嘴里念念有词:“一不做二不休,赌都赌了,老子就往大了赌。”
他把一颗手榴弹拉开弦在小路上设置成一个绊雷。
这回,他们隐入了大路下方的树林里。就像老天爷要帮助他们似的,树林里还有一个干燥的岩洞。吴树林瘫在地上,说:“可以睡个好觉了。”
赵兴旺眼露凶光,对吴树林说:“睡觉也要竖着一只耳朵,不然咋个死的都不晓得!”
吴树林睡下。
赵兴旺还把洞里仔细搜索了一遍,这才放心睡下。
他又说了一遍:“一不做二不休,都怪他们把老子追得这么紧!”
5、调查员
四川某边城,国民革命军某军军部。
参谋长穿着一身长衫,手里端一把茶壶:“我是代表军长。”
三十出头的刘铭说:“我晓得,参谋长是代表军长。”
“从军官训练团结业有一年了吧?”
刘少校一个立正:“一年了!”
“不想待在军部,不想只做参谋工作?”
“卑职不想在后方,想上前线!”
“入训练团前当过参谋?”
“二十九旅,当过两年!”
“再以前是高中毕业?”
“投笔从戎,报效桑梓!军官训练团结业后,我一直申请到抗日前线!”
“你晓得嘛,国府为稳固大后方,本军的任务不是在前方抗日,而是安定后方。建设后方,一样需要青年干才。”
“杀敌心切,还望参谋长成全。”
“你要干得成一件事,我就在军长跟前替你请求。”
“请参谋长明示!”
“哈克里金矿知道吧?”
“知道!那里连出了几次大金子!大家都说是本军本省兴旺的吉兆!”
“可我们和矿上失去了联系,已经是第三天了。一定是电台出了问题。军长的意思,是派一支精干部队,护送一部电台到矿上去。”
“报告参谋长,我就想去的是抗日前线!”
“没有稳固的大后方,哪有什么前线!”参谋长缓了口气,“其实,送电台只是顺便,军长的意思,是任命你为特别调查员,授少校衔。本军辖地汉番杂处,盗匪丛生,民生凋敝,这一路,民情匪情,地理交通,待开税源,均要处处留心。你这支部队,直属于军部,不受当地驻军节制,遇事可以临机决断!”
“谢谢军长栽培!”
“去军需处报到,领了电台,明天就出发吧。”
“不必等明天,领了电台就出发!”
参谋长起身,拍拍他的肩头:“好!军长看人准!汽车都准备好了!”
果然是三辆汽车都准备好了。一连士兵带着电台都坐在了车上。
参谋长说:“本军本省开支浩繁,缺少财源,金矿的事情着实重要。”
调查员说:“卑职一定星夜兼程,把电台送到金矿!”
临行,参谋长又对警卫电台的连长说:“田连长,调查员从军官训练团结业不久,没有赶过长路,你要好生照顾。”
卡车这才开出了军部大院。
这正是吴树林和赵兴旺伴着大金子在山洞里熟睡的时候。
卡车开出军部不久,就进了山。顺河开了一段,就沿着盘山道往山上爬。山很高,要仰头望顶的话,没戴稳的帽子会从头上掉下来。这时,卡车才停下来,在路边客栈吃饭。田连长拿一个包袱给调查员:“参谋长交代我,让调查员换上便装。”
客栈狭窄。刘调查员爬到楼上在老板夫妇的卧房里换了衣裳。
吃完饭再上路,他不坐驾驶室了,和大家坐在车厢里,抬头就可以望到天上越来越密越来越亮的星光。
田连长对他说:“调查员睡一会儿吧,路还很远。”
调查员说:“你们都穿着军装,我穿着这身衣裳。”
田连长说:“你都是少校了,还穿着尉官的军装,不像个样子嘛。”
6、吴树林和赵兴旺
吴树林在岩洞中对赵兴旺说:“班长,天黑了。”
赵兴旺说:“我长着眼睛,我看得见天黑了。”
“我们是不是该上路了?”
“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
“班长你不走?”
“还不到时候。要等那些追兵回来了才晓得往哪里走。”
“趁他们没有回来,还不赶紧走?”
“想死你就走,我说了我不会挡你的路。”
“金子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要有本事一个人弄得起走,你就弄起走。”
吴树林笑起来:“那你还不把我杀了。”
“这个你也晓得,那就好好生生地将就着,说毬那么多废话。”
吴树林坐着,抚摸着金块:“妈吔,好久才能把你换成钱哦。”
这时,路上有了动静。是两个人在走动。他们在路口犹豫了一阵,最终往大路上去了。后来,他们又回来,顺着原路返回去了。
赵兴旺对吴树林说:“不是追兵,是两个喇嘛。”
“班长你咋个晓得?”
“咋个晓得,你长着的是猪耳朵吗?喇嘛皮靴的声音和胶鞋的声音能一样吗?”
“班长你太神了。没有你我咋个走得出去!”
“那你就死在这里,反正走不出去。”
月亮出来的时候,被烟火误导反了方向的追兵们回来了。他们起码有十多个人,在岔路口停住,高声大嗓讨论该往小路上追还是往大路上追。月亮明晃晃照着,他们站在路口争论,有人主张往大路上追,有人主张往小路上追。
“不会走小路,小路通到那么高的雪山上,那是死路!”
赵兴旺听出来那个声音是自己的排长。
“背着那么大坨金子走大路,照样是找死!”
说到金子,争论就变了味道。
“妈的,背着那么大坨金子,要是老子,要多大劲就有多大劲。还不快得跟神行太保一样!”
“要是老子,先找个山洞和金子安安逸逸睡几天,那不比睡婆娘安逸多了?”
“老子可要着急把金子变成钱!”
“我们是追金子的,别做白日梦了!”
“不要让我一个人啊!要是让我追上了,老子就干掉这两个家伙,自己背着金子继续跑,你们就谁也找不到我了!”
赵兴旺对吴树林说:“他们只好兵分两路。”
吴树林说:“那我们就走不了了!”
“那就继续在这里待着。”
果然,追兵们决定兵分两路,走大路的人轻松,马上就走了。走小路要攀上雪山,骂骂咧咧好一阵子,才迈开了脚步。赵兴旺屏住了气。设成绊雷的手榴弹爆炸了。峡谷中山鸣谷应的回声过后,传来受伤者凄厉的叫喊。
那是两个人此起彼落的叫声:“救命!”
“救命啊!”
赵兴旺说:“我不想落命债,我只想把人炸伤。”
大路上的追兵跑回来了。他们不敢再往小路上追,怕还有手榴弹或什么机关在等着他们。
因为两个伤员,这股茫然追击了两天两夜,已经疲惫不堪的追兵就有了撤退的理由。他们抬着两个伤员回矿上去了。
赵兴旺和吴树林把最后的那些野羊肉吃了,这才把金子抬到路上。
月光如水。
赵兴旺特意拐到小路上,在手榴弹爆炸的地方看了一眼。他看见了地下的血迹,还有一个死人,直挺挺躺在路上,身上蒙了一件雨衣。矿上的兵赵兴旺都认识,他没有掀开雨衣去看他炸死的到底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
他回到路上的时候,脸上换上了凶狠的表情。
他们确实加快了脚步,很快就顺路下到了谷底。过了一座木桥,道路又折而向东,漫长的缓坡,山坡光秃秃的,无遮无拦。两个人喘着大气,一直走在大山鼓突的腹部上。天快亮时,眼前出现了黑压压的杉树林。他们隐入一片森林之中。他们本可以继续赶路的,但那坨大金子,用结实的绳子捆着,那些路上磕磕碰碰蹭掉了表皮的地方,发出灿然的金光。
吴树林说:“我们的金子好漂亮啊!”
赵兴旺说:“财不外露,老子就没见过这么招眼的东西!”他从松树上用刀刮下一些松脂,糊在大金子那些新的擦伤处,为的是遮住那刺目的光芒。
他一直不和吴树林说话。
吴树林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凶巴巴地看着他。吴树林那些话当然都是废话,一会儿担心怎么走得出去,一会儿又沉迷于金子变现后的种种幻想。
赵兴旺最后才开口:“你发现这坨大金子真他妈是时候!”
吴树林笑起来:“当然是嘛,要是冬天发现,大雪封了山,哪里都去不了,那不是干着急嘛。”
赵兴旺也笑了:“你就没有想过会为此丢了性命吗?”
吴树林躺在一地柔软的松针上:“不会的,老天爷开眼,给这么大坨金子,是让人享受,不是让人死。”
“老天爷最爱做的事,是让你看得到,又得不到。老天爷是拿这个来折磨人的。”
赵兴旺对吴树林说:“就从这个金矿讲起吧。你晓不晓得刘军长为什么派我们山高水长地来开这座金矿?”
吴树林一个金伕子当然不知道:“因为金子多嘛。”
“刘军长以前可看不上这样的穷山恶水,势力雄壮时手下三四十万兵马,占着四川省税源最丰富的地方。可是好东西哪有让一个人独占的道理,另外几个穷军长合纵连横,把他打败了。好在,全民抗战,一致对外,打胜的队伍都开上了前线。最富的军长,被赶到最穷的地方,人马只剩两三万人,要是不开这里的金矿,手下人没有饭吃,怕是这点儿队伍也要散了。”
“班长晓得这么多事情!”
赵兴旺说:“最后一仗,老子挂了彩,一颗子弹把大腿打了个对穿对过,幸好没有伤到骨头。”
吴树林好奇:“你打死过人吗?”
赵兴旺说:“老子要是不打死别人,那就换自己报销在战场上了。”
吴树林小心地问:“是不是你的手榴弹也炸死人了?”
赵兴旺发作了:“要是为这坨大金子必须杀人,老子首先就把你干翻!”
吴树林躲到一边,蜷缩在松树下面,不敢再说话了。然后,他哭了起来:“我宁肯没有发现这坨大金子。矿上的人都晓得,得了大金子的人都要倒霉。山上的喇嘛都念过恶咒了。”
7、咒语
庙上相信密法的喇嘛们确实在护法神殿里念动了咒语。
从这几天矿上的动静看,确实是出了大金子。又听说,大金子被他们自己的人,一个金伕子和一个哨兵合伙偷走了。
咒术要生效,最好对象明确,画影图形。如果对象只是个名字,或者像这一回连名字都没有,就是偷了大金子的人,两个飘忽的身影,结果怕也就同样飘渺,恶咒也就难以落到这两个人身上。
尽管如此,护法神殿里依然鼓声咚咚。
法王向来对咒术持怀疑态度,此时自然长吁短叹。
襄佐建议:“要不要把师爷叫来,听听他怎么说?”
法王叹道:“他一个瘸子能有什么办法?”
“那就不叫吧。”
“还是叫吧。”
过去庙里没有师爷这个职位。民国以后,封闭的法王世界也多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特别是四川省政府的交往,所以就新设了这个职位:通汉番两种语言,识得汉文书信文告,也能用汉文撰修书信呈文的师爷。
师爷是好多年前从金矿上来的。
那还是袁大总统执政时期,在四川省辖下,这一带地方统称川边,管理这带地方的官员叫镇守使。镇守使在川边推行新政:办学、垦殖、开矿和修路。其他三项没有首尾,开矿一项,在多金的地方易于着手,正所谓吹糠见米,当即就开了金矿多所。藏金最富、出金最多的,就是这座哈克里金矿。那时,新政初兴,金矿和寺庙频起冲突。护矿部队训练有素,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吃亏的总在寺庙一方。后来,袁大总统死了。镇守使转投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倒台,镇守使随之倒台,金矿上发生兵变。护矿部队自己抢劫金子,自己焚毁金矿,一夜之间,法王武装啃不动的堡垒,化火化烟,什么都没有了。只捡回了眼下这个师爷。他是金矿上的文书,揣着十几两沙金,腿被流弹打伤,坐在烧得只剩点儿乌黑框架的废墟旁边。
他被押回庙里。
法王问襄佐:“你说我该拿这个人怎么办?”
想不到这个人听得懂他的番语,还用不太流利的番语作答:“要是法王觉得官军不会再来,您就把我杀了。”
法王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笑容:“我手下这些人确实想杀你。可是官军还是要再来的呀!”
“那就请法王赏口饭吃。我为您执掌和政府来往的书信文告。”
“你是要个官位吗?你要的这个官位汉人叫作什么?”
“师爷。”
法王很轻松地就发出了这两个音节:“师爷。师爷。”
“法王同意了?”
法王对襄佐说:“给师爷安排一个房间,叫人给他治伤。”
再之后,四川本省各路军阀都自己当了军长。当了军长的都想当省主席,在盆地中央打得不可开交,十几二十年没有顾得上山里的事情。直到势力最大的刘军长打了败仗,直到川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国府为稳固大后方,把川边地方划为刘军长辖区,才把办学、垦殖、修路和开矿等项新政重新提上日程。刘军长一纸命令,法王就是他属下的绥靖区区长了。新政初开,首先就不顾法王反对,派部队来重开了这座金矿。转眼间,这金矿开了已近三年。其他新政尚有沿旧驿道新修公路,废了与法王邻近的土司,派去了县长,还在县政府旁盖国民小学和税务所。
师爷瘸着腿来了,望着法王:“法王要给谁写书信吗?”
法王说:“我想问你话。”
“我猜法王是要问金矿上的事情吧。”
“看这几天的动静,肯定是矿上又出大金子了。”
“法王英明,我已经有消息了。两个胆大的家伙,一个金伕、一个哨兵,带着那坨大金子——怕是有五六十斤重的大金子,跑了!那个哨兵还拖走了枪。这个人姓赵,他还用手榴弹炸追他们的士兵,一死两伤。”
法王说:“我们可不可能做点儿什么?”
“当然是要帮点儿忙。”
襄佐说:“师爷你还要给他们帮忙,让他们把金子全部掏空吗?”
“我是说帮点儿倒忙。法王该给扎西首领写封信,把出了大金子的消息透露给他。他闻声而动,东去的道路被封住,那大金子就跑不出法王的地盘。”
“金子落在他手上,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
“人家手里的金子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落在了他的手上?我出此计,是先保证大金子不出无量山就好。”
法王对师爷说:“你有一个好脑筋,不把事情想反了的好脑筋。”
8、一条命
汽车开到了公路尽头。
刚下了一场雨,路上的坑洼变成了一汪汪水,映着天光。
路边的桦林边立着两幢孤零零的房子。木瓦覆盖的房子顶上雾气升腾,散发着甘甜的略近腐败的气息。这是二十四军的转运站。公路继续向西,他们在这里吃了热饭,就转而向南,往雾气萦绕的山中徒步进发。从这里到金矿总共有四天路程。
这天的行程,走到天黑,山谷中有一个种青稞和玉米的番人村子。
田连长说:“这个村子建县早,番人开化已久,可以借宿。如果走到半夜,半山上有一座客栈。”
调查员说:“那就赶到客栈,一来多赶了路,二来顺便调查税源。”
差不多是庙上师爷写好了给扎西首领的信,派一个化装成游方喇嘛的信使上路的时候,差不多是刘调查员一行人在转运站吃过午饭,徒步上路的时候,睡在大金子旁边的赵兴旺醒来了。吴树林仍在熟睡。漏过树枝的太阳光一条条一块块落在脸上。风吹过,那些光的条条块块就在脸上蠕动,他在睡梦中伸手拍打脸上动来动去的阳光。
赵兴旺往地上呸了一口:“拍个屁,又不是虫子!”
他就在这时生起了杀心。
他说:“老子要杀了你。晓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要杀你?不是为了财喜,是因为你就没有享受财喜的福气。”
这时,赵兴旺发现了一头鹿,一路啃着树皮上的苔藓向他靠近。他把枪在大金子上架稳,推子弹上膛时,那金属相撞的声音把鹿惊了一下。但它只是昂起头来,倾听一阵,没有跑开。它再次低头时,枪在密林中一声闷响。鹿软软地倒在地上。
吴树林一声惊叫,醒了过来。
赵兴旺不管他,自己飞快跑到山梁上看枪声有没有惊出什么人来。四野无人。只有几只鹰在天上盘旋。他笑笑,起身又回到松林里去了。
他自己给鹿剥皮,对吴树林说:“老子刚才都想杀人了。杀了鹿,心头好过些,就不杀你了。给老子去林中找最干的柴火。”
最干的柴火是树上的枯枝,这个吴树林知道。
吴树林用捡来的枯枝生了火,林子上面连一点儿烟都没有冒。只有干树枝抖着火苗噼噼啪啪地燃烧。赵兴旺把鹿剥了皮,把肉割成一绺一绺,搭在树枝上烤。然后,才把鹿皮铺在地上,解开绳子,把大金子包好。用鹿皮边缘裁下的一段皮绳,把口子扎紧。鹿皮在火边慢慢干缩,把大金子紧紧包裹起来。
黄昏的时候,松林上的风大起来,松涛震响,两个人像是坐在汹涌的大海底下一样。
两个人吃饱了鹿肉,还有了十几斤肉干。
赵兴旺拿出酒瓶,每人喝了两口:“该上路了。”
这一回,是吴树林背着鹿皮包裹的金子,赵兴旺背着鹿肉,行走在暗夜里的路上。之字形的路,在大山鼓突的肚腹上一直缓缓向上。赵兴旺一会儿跑到前面张望,一会儿又落在后面,倾听有什么动静。直到吴树林说:“班长,歇口气吧,实在是走不动了。”
赵兴旺语气凶狠,用枪口顶着他背上的金子:“走!走!”
直到吴树林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
这时,月亮升起来了。月亮升起的时间,一天晚过一天,这一天的月亮升起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吴树林哭了。初二十一,天上的月亮只剩下小半个,在他的泪光中晃晃荡荡。他对赵兴旺说:“我再歇口气,就有劲了。”
赵兴旺给他吃了两颗水果糖,又喝了一口酒:“你自己找的罪受。”
“班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赵兴旺帮他站起来,重新迈开了步子。望见山口的时候,吴树林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大金子哭了起来。
赵兴旺说:“是不是后悔不该发现这块大金子了?”
“要是这金子小一点儿就好了。”吴树林哭着说,“要不,我和你现在就把这大金子分了。”
“怎么分?拿什么分?你倒是分给我看看。”
赵兴旺自己把大金子背起来,往山口走去。赵兴旺不忘提醒帮他拿着步枪的吴树林:“枪在你手里,可不要生歹心,想把我打死,好独得这金子。”
吴树林还在哭:“打死你,我一个人怎么把这坨大金子运得出去!”
赵兴旺笑笑:“你其实是说,要是有本事运这金子,你肯定会打死我。”
“但凡是个人,哪个不想独得这么大坨金子。”
“这倒是实话。”
两个人只顾着说话,只顾着拼命往山隘口走,背后上来了人也没有听见。那是寺庙派出的信使。这个人急急赶路,手举着游方僧人扎满旗幡、缀着念珠的小幡幢,超过他们时都没有停留。他只操心师爷以法王口吻写的信,能不能按时送达。这两年,扎西首领和他的队伍,整天被刘军长的官军追着,行踪飘忽不定。现在,他只是往前走,到底走到哪里,还要靠一路打听。他当然认得这两个人都是金矿上的,一个是金伕,一个是哨兵。路上行人,当然会背负着东西。他是第一个与大金子错身而过的人。
信使的脚步在背后嚓嚓响起时,赵兴旺惊出一身汗来。他想向吴树林要枪,吴树林却站下来,挪不动步子,隔自己有十几步远。赵兴旺只好继续挪步向前。身后嚓嚓的脚步声听起来就充满了力量,他只等着一记重击落在身上。但那个人越过了他。目不斜视,往前方去了。
吴树林赶了上来:“那个喇嘛没有看见!”
赵兴旺从他手里夺过枪拄在地上,喘了半天,才重新挪动脚步。
到山口时,天已经亮了。回顾,身后的路盘旋向西。前望,身前的路顺着山势一直下到谷底。峡谷的底部,有补丁样一块块斜挂在山坡上的耕地,和一个孤零零的村落。赵兴旺把金子让吴树林背上,两个人一路向下。地面袒露,碎石满坡。至少要往下走七八里,才进入森林地带。
吴树林请求休息,赵兴旺不准:“再提这事,老子就把你了结了。”
在距森林还有四五里路的碎石坡上,吴树林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路边。沉重的金子带着他向坡下滚去。滚到半途,金子脱了肩,人瘫在乱石间,脱了肩的大金子继续滚向山下。赵兴旺就像滚在坡上的是自己,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他看见大金子撞进了树林,撞击在树上发出巨大声响。直到响声停在了树林中间,他才定下神来。
赵兴旺顺坡下到吴树林跟前,他已经摔得不成样子,有进气没有出气了。他大睁着的眼睛水汪汪地浮着天上的白云。
赵兴旺对他说:“死了就死了,还把眼睛睁这么大,不甘心吗?不摔死我也得杀死你。你说得对,但凡是个人,没有人不想独得那么大坨的金子。”
吴树林眼神里也有了凶狠的神色:“我命里没有。你命里也没有。”
“那我得试试。我得跟老天爷争上一争。”
“我的罪受完了,你的罪还没有受完。”
“快咽气吧,金子还在下面等我。”赵兴旺说,“等我把金子变了钱,我会给你烧纸,烧三个老婆,两座房子,都带院子。”
吴树林喉咙里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头一歪死了。赵兴旺替他把眼睛合上。还把他身上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一把短刀、一盒火柴、两沓子纸币,再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的身子本来就卡在石缝里,捡些大块的石头很快就把他的尸体盖上了。
“真是个穷鬼。太穷的人怎么消受得了这么大的财喜。”赵兴旺又往那堆石头上淋了小半瓶酒,“你是个好人,没有让我多落条命债。刚才你要是不咒老子,我就把整瓶酒全给你了。”
很深的峡谷里,一条蜿蜒的大河在闪闪发光。
赵兴旺说:“无量河,过了河,再翻过无量山,大金子就是我的了。”
…… ……
节选自《人民文学》2022年1期(责任编辑:李兰玉)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九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