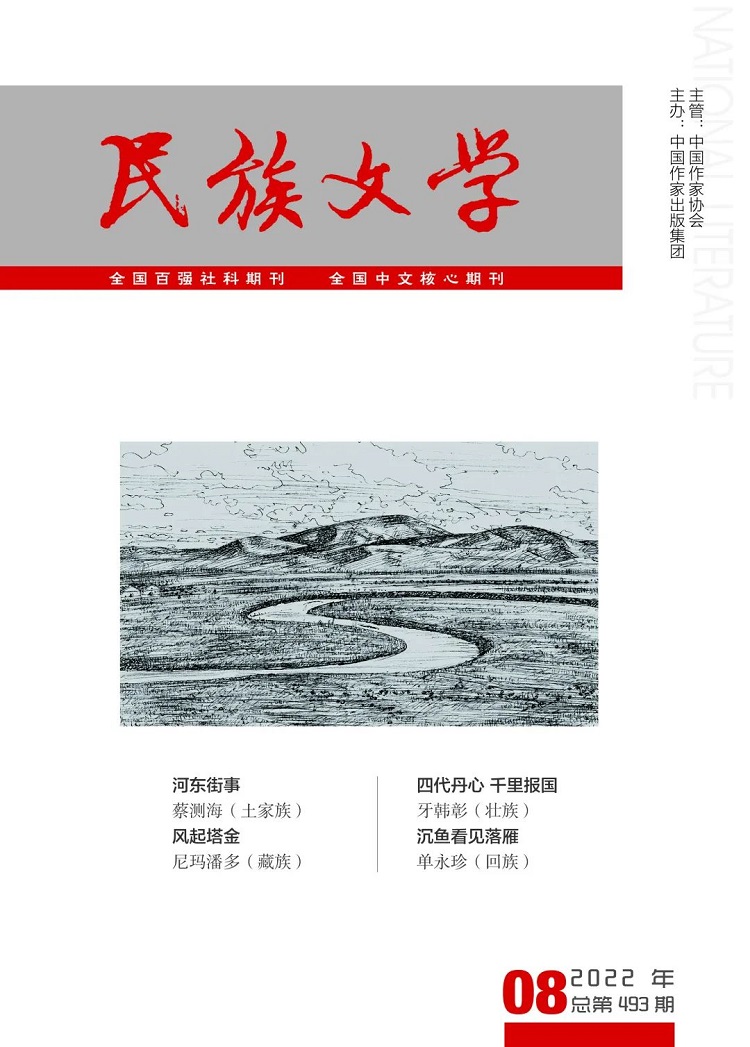
第一章
一
藏历新年才过,公历已进入了三月中旬。
迎接春天的日子,是塔金的风季。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无休无止的风,把塔金人的好脾气磨到不时擦出火星子,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塔金人的另一种修行,不喊杀不骂天,就算修行到家了。
风和雪是塔金的特产。和漫长的大雪封山相比,梅朵曲珍觉得风算不了什么,人被困在原地,牲畜找不到草啃,那才让人心塞。何况风季过后,塔金将迎来最美的夏季。她年轻时,就给不喜欢风季的朗杰多吉说:“春天的风,是塔金的产前痛,她将生下一个美丽的夏天。”朗杰多吉说:“这是你这个大老粗说出的最富有哲理的话。”她不懂什么叫哲理,但觉得它一定是好东西,每当有人诅咒塔金的风,她就会搬出这个比喻。
今年的风,比往年来得更猛。梅朵曲珍的抹布不停地在茶桌、窗台和柜子之间移动,将室内的积尘抹得干干净净。白玛措吉已多年没有感受塔金的春天了,一回来就遇上狂风大作,看着无处不钻的尘土,加上心里憋闷,忍不住诅咒这鬼天气。梅朵曲珍停止擦拭,诧异地望向时髦的女儿,慢悠悠地说:“天也骂地也骂,不怕积口业也不怕遭报应啊。积口德就是积福报,有福报诸事才顺。”
白玛措吉眼下最烦的,就是提顺不顺的事,半句也听不得,气呼呼地回敬道:“爸啦也骂,你怎么不说他。”
没等梅朵曲珍说话,朗杰多吉自我澄清道:“我骂的可是风,没骂天也没骂地,地方还是好地方。”好像骂风,比骂天地的罪孽要轻一些。
梅朵曲珍取下护腰扔到卡垫上,“你爸啦骂风骂雪,还不是走不出塔金半步。这说明福报很重要,别动不动造口业损了福报。”
朗杰多吉瞪了她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走出塔金,何年何月何日?说出来让我听听。”
梅朵曲珍还真说不出一二,他可不像她,他有什么都藏在心里,更不会说出要走出塔金,可一举一动不都透着想走的意思吗?梅朵曲珍不敢这么说,在一次争论中,他一字一顿地对她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心思。
“当——当——”柜子上的座钟,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长毛招财也跟着吠叫了几声,像是补充报时。一家三口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座钟,白玛措吉发现时针和分针齐齐地指向了十二点。
座钟像是提醒了梅朵曲珍,她撑开胸兜,拿出一个更软更小的帕子,擦拭座钟,擦到雕花处,还把帕子拧成细绳,穿来穿去。
这几天,梅朵曲珍家里的风,不比外面的小,这阵风吹走了往日的温馨。朗杰多吉戴着老花镜,拿着一张被塔金的烈日晒黄的报纸,将脸深埋其中,除了偶尔接过老伴儿递来的茶,很少抬眼,一副沉浸于阅读的样子,只是不时的叹息声出卖了他。梅朵曲珍藏袍的胸兜鼓鼓囊囊,装着和狂风作战的“武器”。风卷着田地上的浮尘,飞到窗台上、茶桌上,她用胸兜内的抹布,耐心地抹去,不让它们在上面停留很久。白玛措吉跟梅朵曲珍斗嘴后,就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卧室里。以往,梅朵曲珍总是先软下来,把茶和吃食端到楼上,左哄右劝。她常感叹,在这个家里,她的地位最低下,要巴结这个伺候那个,结果还是不讨喜,连长毛招财这小畜生,都有人摸一摸抱一抱,唯独她没人疼。这些天,她也硬下心来,习惯被哄的白玛措吉只能在卧室来回踱步,自己宽慰自己,偶尔驻足窗前,望望别家屋顶上飘扬的经幡。新年才挂上的五色经幡,架不住塔金暴烈的风,已成了破布片,不由自主地左飘右荡。
每个人不就是风中的经幡吗?随风起舞,随波逐流。有几个人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白玛措吉看着眼前的风景,想着自己的处境,一阵惆怅。她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桌上放着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她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看这本书,书上划着各种颜色的线,翻开的那页上,有一段话被她打上了着重符号:“我虽然常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我的指路星在哪里?”她自言自语着放下书,又回到窗前,眺望着远方。
远处的山头布满积雪,神秘又宁静。她知道雪山脚下,有许多隐修洞。据说在百余年前,塔金是隐修者的圣地,遍布着修行的男女,他们想以赤心归于自然,不喜不怒不争不抢,可最终到底有几个做到了呢?她真的希望能看到他们当中某人的传记,她想知道没有欲望的人生真的存在吗?
几个月前,她还在校园里畅想着未来。那时的她,是那样憧憬毕业后的日子,那样心急,恨不得早一点尝到未来的滋味。她最好的朋友夏荷,看上去温顺绵柔,却特别有主见,她说,未知的未来才刺激才好玩,如果什么都清楚了,还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那时的夏荷,已经做好了到沿海城市打拼的准备,她甚至劝白玛措吉也跟着去闯荡。
毕业分别前一天,她俩去了常去的那家面馆,破天荒喝了几瓶冰啤。白玛措吉举着杯子说:“大山的孩子应该回到群山间,我不适合沿海,更不适合漂流,倘若你混不下去,也可以来群山间找我,我们一起在塔金隐修,那里是隐修者的圣地。”夏荷满脸红晕,晕晕乎乎地举着杯子说:“人的一生,一定要去闯荡,一定要去争取。”
二
白玛措吉本该在去年秋天回塔金,拖了数月才回,完全是朗杰多吉的意思。
对于白玛措吉毕业后的去向,朗杰多吉很早就有了主意,当然,他是不会告诉梅朵曲珍的,他不想让她感到不踏实。每当他给女儿写完信,都要念一遍给她听,问一下还有没有需要特别嘱咐的事。朗杰多吉比梅朵曲珍的心思缜密,有些小事她想都想不到,他却能考虑周全,嘱咐的话,自然没有一句要加。在这个家里,除了上班,梅朵曲珍还揽下家里所有的活儿,一封沉甸甸的信写完,也是梅朵曲珍亲自送到县城邮局。每次她都会在信里夹一朵干花,这么做也是听朗杰多吉说,他家的信件必夹一朵干的优昙婆罗花。无意中说出的话,让她感觉那么美好,此后的每个夏天,这个大大咧咧的女人要摘几把野花晾起来,一朵朵地寄给她的女儿,让她闻到塔金的花香。她这么做的时候,万不会想到,丈夫在每封信里必然叮嘱一件事:一定要学习好表现好,想方设法留在拉萨,千万不要回到塔金。
小时候的白玛措吉,是学校里的小明星。“六一”的校园活动,上台代表学生发言的一定是她;学校编排的舞蹈里,她一定是站在最显眼的位置,脸上扬着当地孩子少有的骄傲;鼓号队里,她就是那个戴着奇怪的帽子,举着指挥杖的小家伙。
梅朵曲珍看着举着小棒子煞有介事的她,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说:“我怎么生了个脸皮这么厚的孩子,干什么都不胆怯。”这种情况下,朗杰多吉会立刻反驳:“怎么能说是脸皮厚呢?见过世面的与没见过世面的,是不一样的。”朗杰多吉乐于看见白玛措吉的表现,他觉得她的未来可期,他的返城愿望有可能在她这里实现。
毕业分配和朗杰多吉的期望刚好相反。在白玛措吉身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得到这个消息,朗杰多吉急了,向来清高的他,拉下脸面,联系了原来的同学、一起下乡的知青,四处托人找关系,整整半年时间,朗杰多吉在塔金心急上火,白玛措吉在拉萨焦虑不安,本就对拉萨没有多少兴趣的她,被焦灼得更没有心情了,她只想回到塔金。朗杰多吉却一次次发电报:请勿回来。在他心里,她一回来,希望就泡汤了,所有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后来,也不知他在哪里碰了一根硬钉子,终于妥协了,发了一封仅有“回塔”二字的电报。白玛措吉从那两个字里,读出了深深的无奈与绝望,但这两个字,也让她得到了解脱,接到电报的瞬间,她有了久违的轻松感。
朗杰多吉从女儿考上大学的那刻起,就在憧憬她的未来,毕业留拉萨工作,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塔金县城还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考得那么好。可是,一纸派遣证又把女儿完完整整送回来了。其间,他的妹妹强珍来信说,为工作的事,孩子都憔悴了不少,还是趁早做个决定吧,或者回去工作,或者干脆不要这份工作。后面这个选项,从来都不在朗杰多吉的计划中,传言说,再过几年,西藏也不包分配了,这份工作绝对不能不要。
白玛措吉以往假期回家,朗杰多吉总是先到县小车班打听一下,看有无到拉萨出差的车子。朗杰多吉在塔金县算得上德高望重,大家都买他的账,白玛措吉只需在强珍家等着,就有车子到门口来接。这一次,“回塔”二字之后,再也没有任何音讯。这大半年在姑姑强珍家无所事事,连平常最淡定的姑父阿旺都着急了,听说朗杰多吉让她回去,亲自出门帮她找车,嘴里直唠叨:“赶紧回去吧,别寺院的茶没喝上,连村庄的粥也错过了。”
强珍白天在茶馆忙碌,茶馆歇业就到劳动文化宫摆摊,正在赚钱的劲头上,看着她收拾行李,就在一旁泼冷水,“要是我呀,就在拉萨做生意,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干吗。现在单位上的人,都停薪留职做生意。按这形势,以后挣钱会越来越容易。别看你上过大学,骨子里跟你爸一样,中规中矩懦弱虚荣。年轻时我阿妈让他回来,让他像我阿爸那样做生意,他就是不回来……”
阿旺打断她的话,说:“过去的事就别说了,我看措吉回去也是对的。有一份工作到底还是稳当一点,也不用担心政策会不会变。”
强珍不理会阿旺,继续说:“阿妈在世时,只信任哥哥。她总说我浮夸说我不靠谱,可我在拉萨活得好好的,她那个有文化的儿子……”
强珍的这些话,白玛措吉听得太多,只管左耳进右耳出。阿旺却觉得过意不去,厉声嚷道:“强珍,你闭会儿嘴不行吗?孩子都要走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少,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让白玛措吉诧异的是,在塔金路口,只有梅朵曲珍一人在狂风中等候。“阿爸呢?”这是她下车的第一句话。梅朵曲珍却忙着把一包东西塞给司机,没有搭理她。只听见司机说:“可以可以。”梅朵曲珍把她推回车内,自己也费力地挤上车,指挥司机把车子开到家门口。
朗杰多吉顶着花白的头,穿着开襟的毛衣,神情落寞,完全没了平日的爽朗,他接过白玛措吉的行李,歉疚地把手搭在她的背上,一句话没说,完全没有父女见面的欣喜。
送走车子的梅朵曲珍像换了一个人,一边给白玛措吉的木碗倒热茶,一边细细端详她,满脸含笑。
“瘦了一些,瘦就瘦点吧,没病没灾就好。”
受朗杰多吉的影响,白玛措吉原本高涨的情绪低落了下去,对阿妈的话没有反应。
“算了吧,这点小事就苦成这样,又没有出人命。这样阴沉着,连好运气都跑没了。”梅朵曲珍眯眼怜爱地看着女儿,话是说给老伴儿听的。
“是啊,塔金也不错。”朗杰多吉敲着沙发扶手,悠悠地说。
“明天就让松巴一家过来吧,他们早盼着她呢,很早就问我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盼什么不好,非要盼她回来,以后有的是时间,先让孩子休息吧。”
梅朵曲珍张了张嘴,把话咽下去了,手捋着白玛措吉的长发,笑脸上爬满了皱纹,“头发都卷成羊羔毛了,不过还真好看。”
“有啥好看,女孩子朴素一点好看。挂那么长的耳坠,像只放生羊。”
“我觉得好看,我年轻时没打扮过,看着女儿打扮就是喜欢,年轻人就应该打扮。”
“那你也戴呗,嫌不够大,就把自行车轮胎戴上。”朗杰多吉说完难得地笑了起来。
这一笑,让气氛轻松了一些。不过也就是一阵,没过一会儿,朗杰多吉的叹息声,又把刚提起来的气氛拉沉下去。在这个家庭,他是主心骨,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他的心情,决定了整个家庭的气氛。
三
朗杰多吉的拉萨人身份,在塔金县城无人不知。那一口优雅的拉萨口音,已成为他的标志。
在塔金,拉萨哇(拉萨人)就是他的名字,偶尔有人说起他的真名,对方总会愣一下,然后敲敲自己的脑门,恍然大悟的样子。
朗杰多吉在塔金的与众不同,不仅因为一口拉萨话。在很长时间里,他是帕当乡最有文化的人。帕当乡还被称为帕当区时,大家都叫他知青朗杰多吉啦,拿着纸墨,请他写信的村民排成队。后来到塔金县城工作,大家都叫他拉萨哇朗杰啦。这个“啦”字,包含着尊敬与崇拜。有些人的“啦”只是当面一叫,背地里直呼其名,朗杰多吉啦的这个“啦”,已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背地里骂他,也去不掉这个“啦”,仿佛已经长在了他的身上。
白玛措吉生在塔金长在塔金,也说得一口好听的拉萨话。在白玛措吉说拉萨话这件事上,朗杰多吉可费了不少心思。他宁愿毁掉慈父形象,爱唠叨、爱发怒。和小伙伴儿在一起,白玛措吉觉得用塔金话更自在,回到家里,照顾父亲感受,语言系统切换到拉萨频道,但总会不小心冒出一两句塔金土话,一双怒目或者一声呵斥是常事。那时的她,常常纳闷,身在塔金,为什么非要说拉萨话。
在塔金人眼里,拉萨是遥不可及的梦,是一座虚幻的城市,所愿所望都在那里。旧时塔金的高僧大德,向往的终极是拉萨,拉萨的三大寺,是他们眼中的日月星辰。塔金的大人逗弄小孩子,喜欢用双手夹着脑袋提起来问:“看到拉萨没有?”孩子们经不住这般痛,迫不及待地回答:“看到了看到了,还看见了大昭寺的觉悟佛(释迦牟尼佛)。”也有顽童不怕疼,大喊:“没看到,影子都看不到。”大人可不会轻易饶过这些顽童,抓住了就要扯着耳朵往上提,手刚摸到耳朵,根本用不着使劲,他们又大嚷:“看到了看到了,连供桌上的供品都清清楚楚。”大人这才满意,松开手,骂一声,饿死鬼。
那时,白玛措吉听大人们说起拉萨,会扬起小脸骄傲地说:“拉萨开在一朵八瓣莲花上。”这句话,当然也是朗杰多吉教她的,从他嘴里说出来,不觉得多有深意,从白玛措吉的小嘴里蹦出来,拉萨瞬间充满了梦幻,恍若仙境一隅。其实,那个时候,她还从来没有到过拉萨。每次过年,他们回的都是东孜的姑奶奶家,自己和拉萨的那层关系,她搞不明白。白玛措吉这么一说,就会收到一双双爱怜的眼神,还有人摸摸她的脑袋,仿佛她的身上也有拉萨的仙气。在这样的情境下,白玛措吉就会生发出表演欲望,会继续扬着小脸说:“你们知道协噶林巴·明久伦珠吗?你们知道他的《忆拉萨》这首诗吗?”到了这个阶段,听她说话的人基本摇头,也没人追问这个叫什么伦珠的是干什么的。
朗杰多吉刚结婚那阵,喜欢喝酒,梅朵曲珍总是把头道酒倒给他。他的酒量小,用不了多久,就会喝醉,然后趁着醉意背诵一段《忆拉萨》,成了规定程序,也是一到这个环节,梅朵曲珍的家人该上茅房的上茅房,该喂牛喂马的赶紧趁这工夫,让朗杰多吉的乡愁飘在空气中。那时候,朗杰多吉喝醉酒是要哭的,乡里人保守,他没法抱着梅朵曲珍哭,就把脸埋到双腿间,边哭边说:“我没处说话。”
“那么多人在这里,怎么没处说话呢?”
“你们听不懂。”
“你大声一点,我们就听清了。”
“你们不懂……”
四
白玛措吉考上大学,是朗杰多吉最得意的一件事,借着这事,他把梅朵曲珍好好地数落了一番。“只看得见鼻尖的人,怎么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他说这话时太得意,笑出了声,捧在手上的甜茶也洒了一桌子。
梅朵曲珍边擦边说:“她一直很用功,从哪里考都能考上大学。”
白玛措吉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在塔金念中学,被朗杰多吉送到拉萨读书。那么小就让她离开家,让梅朵曲珍一直耿耿于怀。
“你没上过学,不懂的,学习环境很重要的,知道吗?”
梅朵曲珍似懂非懂地说:“不是说还要比别人多读一年吗,有什么好?”
“这叫预科,她那么小,多读一年算什么,出来就是名牌大学毕业,不一样。我说你最远只看得见鼻尖,你还不高兴。”
“那毕了业就能分个好工作,是吧?”
“那是当然的。”朗杰多吉那语气,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中。
最恼人的是梅朵曲珍娘家人的各种问题。朗杰多吉在梅朵曲珍家里所受的尊敬,远超女婿的待遇。他的大舅子松巴完全把他当上师看,不时向他请教,每请教一次,他的敬仰就增加几分。塔玛的乡邻问起他的妹夫,他只有一句话: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就是这样尊敬朗杰多吉的人,在白玛措吉上大学的事上,也惹得朗杰多吉很不高兴。
“多上一年的话,以后拿的证,是不是比学四年的硬气一些?”
“一样的。”
“那出来以后,工资是不是比四年的要高一些?”
“不会的,也一样。”
“那好在哪里呢?”
“怎么说呢?那个学校特别有名气,在全国知名度很高。”
“有名有啥用呢?”
松巴的这个问题,朗杰多吉都不屑回答,转而不语。松巴以为博学的朗杰多吉无言以对了,继续说:“一年里可以做很多事的,光工资就能多拿一年嘛,结婚生子也早一些。”
“账可不能这样算。”朗杰多吉转过身子,看着别处说,“不是这样的算法。”
松巴从他转身的动作,看出了其中的含义,便不再多话。
没有上过大学的朗杰多吉,对女儿上大学这件事的张扬,让梅朵曲珍都有些诧异。一向内敛的朗杰多吉,在这件事上,高调得有些夸张。他请松巴宰杀了两头绵羊,又让梅朵曲珍翻出早就不用的陶锅,在家里酿了青稞酒,把走得近的亲朋同事,分几拨请到家里庆祝。“塔金县城去内地上学的孩子也有几个,人家都是悄无声息地来去,没见弄那么大的动静。”梅朵曲珍偶尔也不顺着朗杰多吉,说出这么一两句。他却是一副解释都嫌费口舌的表情。
自从白玛措吉到拉萨上学后,朗杰多吉在家里说得最多的也是考学的事。梅朵曲珍多少还是知道有一些区别,她是故意这样说。共同生活近三十年,她怎能不知朗杰多吉的心思。女儿的走出去其实就是他的走出去,看到他难得张扬,她高兴,也难过。她知道朗杰多吉来到塔金时,比现在的白玛措吉还小,想到这点,她会释然一些。
......
【创作谈】缘起与宿命
在写作完长篇小说《紫青稞》后,我一直有个愿望:写出一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作品。随着时间的延绵,随着周遭各色人物的不断走入与走出,完整地呈现出时间与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和转变。
后来,白玛措吉出现了,并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在不断地想象中,关于她的故事,关于她们家族的故事,日渐清晰起来,当这个故事在电脑上敲击成文字时,又不断地扩展和删减,成型后的小说,和我最初的想象有了不一样的面目,也许这就是小说的宿命,也是白玛措吉的命运,人生的每个站点都不可预测。
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与我不同的际遇,但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结,成长中的泪水、微笑和感叹,都来自于我内心深处,带着真诚的思考与反省。
当《民族文学》决定要刊出这部小说的缩略版《风起塔金》时,我对这个故事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缩写的过程,给我一个很深的启示:繁与简,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魅力。就像舞台上的灯光,用删减的方式聚焦到白玛措吉的身上时,她的棱角更加突出,故事更加难忘,而其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浓度丝毫没有淡化,这不能不说在意料之外。
我一直把《民族文学》视为我写作生活的娘家,她在我的写作道路上,给予了我太多的关爱,这次,从交稿到推出,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为了她的顺利推出,各位编辑轮番与我沟通、交流,仅标题,就有了七八个备选,重视和负责程度,让我感受到作为文学编辑的严谨,也让我感受到了编辑部对作者的厚爱,在此深深致谢。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8期(责任编辑:安殿荣 张金秋)

尼玛潘多,藏族,中国作协会员、西藏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第二十八届高研(深造)班学员。作品曾刊《作品》《民族文学》《长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青年文学》《西藏文学》等刊物,有作品曾入选《追寻她们的人生》《西藏行吟》《西藏的女儿》及《民族文学》杂志社成立30周年优秀文集等,已出版长篇小说《紫青稞》并被翻译成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及英文出版。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散文集《云中锦书》(合著)获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