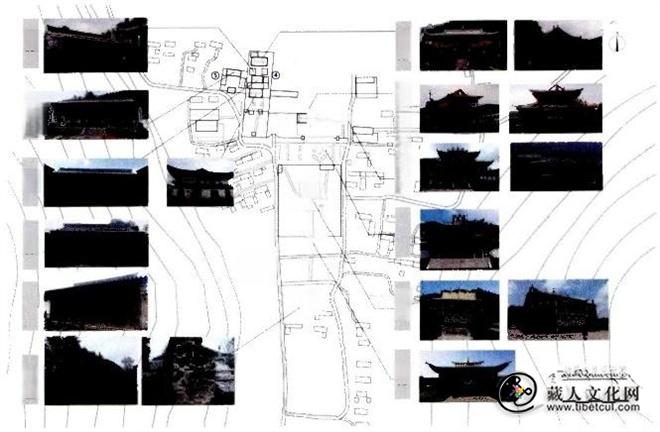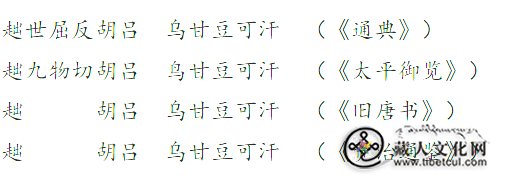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藏文传记文学因其文学和历史的双重特性与宝贵的文化价值,成为近百年汉藏文学翻译领域内一个重要的选材方向,备受译者青睐,产生众多翻译著作。文章试图在藏学学术史视域下梳理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的发展脉络与主要译本,以此全面呈现该领域的翻译成就。同时,也探讨译著产生的社会语境、文本特征和各种翻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为汉藏翻译史提供一定参照。
关键词:藏文传记文学;汉藏文学翻译;藏学学术史
引言
从口头传说、碑刻文献、敦煌写卷到藏传佛教高僧传和民间英雄史诗,藏文典籍中讲述历史人物生平故事之传记文学数量巨多,是认识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20世纪以来,随着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和中国边疆研究的不断发展,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在藏学领域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取得很大进展。回顾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历程,不仅能掌握
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也能对往后藏文传记文学翻译实践给予一定启示。
一、20世纪20—40年代藏学与藏文传记文学汉译
20世纪初中国佛教改革运动中汉藏佛教交流出现新气象,而民国时期的边疆危机又促使国内学界关注边疆问题。因此,随着20世纪初汉藏佛教交流活动和中国边疆研究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包括藏文传记文学在内的藏文典籍汉译成为近现代藏学领域一项重要学术事业。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史上不仅有藏传佛教高僧前往内地弘法,也有汉传佛教僧侣前往涉藏地区研习佛学,两者都对藏文传记文学汉译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弘法有效推动了藏文传记文学在汉语圈的传播。例如,1930年康定喇嘛多杰觉拔格西口述并由其弟子张心若(又名死灰居士)笔录完成的《木纳记》是较早一部汉译《米拉日巴传》,该作于1940年刊登于《佛化评论》。其次,汉传佛教僧侣进入涉藏地区研习佛学时也翻译了部分藏文传记文学作品。例如,1925年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欲前往西藏,但当时因原西藏地方政府阻挠,其成员一时只能驻留西康学习藏语及藏传佛教。法尊法师作为彼时辗转西康赶赴西藏学佛代表人物,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典籍互译和广传佛法事业,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1925年法尊法师前往西康甘孜扎噶寺学习并于1927-1928年摘译出《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两部藏文高僧传[1],译作后来刊登于1935-1936年《海潮音》。
民国时期入藏学佛者欧阳无畏(又名欧阳鸷)也是当时藏文传记文学汉译重要译者。他于1933年入青海藏文研究社学习藏文,后于1934年随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青海省政府委员黎丹率领“西藏巡礼团”入藏进哲蚌寺学习,并于1935和1944年分别译出《宗喀巴大师传》与《德格土司世传译记》(又名《吉祥历代德格法王传·妙善诸事顺意》)两部藏文传记文学作品,可惜前者毁于战乱之中,已无从追寻[2];后者系第45世德格土司泽旺多吉仁增(1786—?)之作,原文为韵文体,欧阳无畏为便于读者阅读未选择直译,而是删节冗赘,以散文体译出,再附《德格土司世系表》,该译作刊登于1945年《康导月刊》第5-6期,后来任乃强根据此译本完成《德格土司世谱》[3]。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面向边疆的研究团体,其中几个代表性藏学学术团体,如康藏研究社、西陲文化研究院、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青海藏文研究社等机构有效推动了当时的藏学研究与汉藏翻译事业。无论从汉藏对照词典编纂的角度,还是从翻译人员培养的层面,这些团体及相关人员对当时乃至此后一段时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都起到重要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安宅、于式玉、王沂暖三位藏学家分别来到甘南和西康,其中李安宅夫妇先在甘南进行社会考察,后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从事学术工作,期间于式玉女士摘译《玛尔巴传》中关于达玛夺得的故事段落并以《西藏大德<玛尔巴传>中的“借尸还阳”故事》为题发表于1946年《大中》第1卷第7期。几乎同一时期,王沂暖由南京经武昌来到四川,先进西陲文化研究院,后入汉藏教理院。1940-1945年间,他先后两次进入西康并于1946-1947年译出《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4]。
著名汉藏翻译家刘立千既是康藏研究社成员,也是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1932年他执教于康定,1944年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副研究员,1946年加入康藏研究社,期间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文典籍翻译工作。就藏文传记文学翻译而言,刘立千于1945-1946年译出乳毕坚赞(1452-1507)《玛巴译师传》并连载于《康藏研究月刊》1946年第1期至1948年第22期,该作成为当时认识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材料。《康藏研究月刊》编者就曾言:“西藏六大教派的祖师传记,是他文化结核的放射线,要了解西藏,非先了解他不可。”同一时期,刘立千还译出乳毕坚赞另一部藏文传记经典《米拉日巴传》,但当时条件有限,书稿未能及时刊印[5]。
总体来看,20世纪20-40年代,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初具规模,虽然译本数量有限,但选目具有代表性,包括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阿底峡(982-1054)、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1012-1097)及其弟子米拉日巴(1040-1123)、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罗桑扎巴(1357-1419)四位高僧的传记,以及历代德格土司世系传记。从译者身份来看,既有入藏学佛汉传佛教僧侣,也有步入涉藏地区考察的边疆研究学者,他们成为当时推动藏文传记文学汉译事业的专业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译者都有驻留康藏的相同经历,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目的。概言之,20世纪上半叶前往涉藏地区学习藏传佛教的汉族僧人和进入边疆考察的学者们都深刻认识到藏文传记文学在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并选择代表性文本加以翻译,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也为后来藏文传记文学翻译与研究起到奠基性作用。
二、20世纪50—70年代藏学与藏文传记文学汉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藏文化交流和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0年代初国家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各地陆续设立民族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批汉藏翻译工作者。相比民国时期大多依附于个体的学术团体,此时国家支持下的机构有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政府制定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计划等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语境下,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出现了新局面。首先,部分民国时期译著的正式出版为藏族文学和文化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代表性成果为1949年12月出版的王沂暖译《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此书于1955年再版发行,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部藏文传记文学汉译本。其次,也有新的藏文传记文学汉译作品问世,其中两部译作较具代表性:一为1957年法尊法师译喜饶嘉措大师(1889-1968)撰《宗喀巴大师赞》(又名《宗喀巴大师传略十七颂》);二为1962年段克兴译格西夹杜日娃赞巴(约12-13世纪)等著《阿底峡尊者吉祥燃灯智传》。《宗喀巴大师赞》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由喜饶嘉措大师专为西安广仁寺所写,全文“共十七颂,用藏族传统九言格律诗写就”[6],其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朴素易懂,不仅是一篇充满古典美学意味的当代藏语诗歌体传记,更是新中国初期汉藏佛教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法尊法师译文语言古朴、形式对等,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阿底峡尊者吉祥燃灯智传》是阿底峡大师众多传记中编纂时间较早的一部传记,文字朴实、记述细致[7],对了解阿底峡大师生平与藏文传记文学写作传统有一定价值。段克兴译本内容完整,忠实原文,译作于1981年由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内部刊印。饶有意味的是,两位译者均是1930年代前往西藏学佛人士,可见这一经历对译者翻译惯习产生较大影响。另外,1930年代进入康藏地学习藏传佛教的张澄基于20世纪50-60年代将《米拉日巴传》译为汉英两种文字[8]。除此,庄晶自言于20世纪50年代译有《仓央嘉措秘传》[9]。
通常,1966-1976年被视为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沉积期[10],此时鲜有藏文传记文学作品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末期王尧翻译的《敦煌本古藏文历史文书》(又名《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译者曾言:“(那时自己)只好把于道泉先生慨然相赠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巴考等人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P.T.1286、1287、1288等若干写卷的法文译注解读本)藏诸箧中,以待时机,而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的讲座稿中,略加介绍而已。”后来,在“五七干校”的三年中断断续续完成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翻译[11]。王尧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包括三大部分,分别为P.T.1286号敦煌藏文文献《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T.1287号敦煌藏文文献《吐蕃赞普传》、P.T.1288号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其中P.T.1287号敦煌藏文文献是早期藏文传记文学重要文本。其实,20世纪50年代王忠和王静如也依据藏文拉丁转写和法文译本翻译过这部文献,只是他们并非从藏文直接翻译[12]。王尧译本于1978-1979年分别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和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内部油印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来吐蕃藏文传记文学的译研事业,也为敦煌吐蕃史料研究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极其重视民族文化事业,藏学研究在人才队伍、机构设置、基础资料整理等方面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呈现出崭新面貌,无论是民国时期译作的正式出版,还是其他藏文传记文本的翻译都为新中国藏学事业提供了有益参考,尤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汉译本对后来藏文传记文学发展史、敦煌藏文文献及吐蕃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20世纪80—90年代藏学与藏文传记文学汉译
1980年代初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又先后建立了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藏学研究机构,有力带动了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13]。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复苏和发展,藏文传记文学汉译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
从外部因素来说,相关组织机构的支持是此时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出版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工作人员为相关学科提供基础材料而翻译不少藏文传记文学作品,其中两项工作较为突出,即前期译作的整理校注和有组织性翻译。第一,1980年刘立千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后,他便考虑整理校注过去译稿,这一工作也得到机构支持。因此,他在1946年译本基础上,依据197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排印版本重新修订《米拉日巴传》汉译稿[14],形成最终译本。同一时期,王沂暖也对《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中个别词汇翻译进行修改,并更名《米拉日巴传》加以出版。另外,王尧和陈践也修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二,1984-1987年青海社会科学院组织人员前往塔尔寺普查整理藏文文献[15],此后又组织翻译团队从事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工作,代表性成果为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五世达赖喇嘛传》(又名《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陈庆英和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成就大海之舟》和《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蒲文成译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七世达赖喇嘛传》,许德存和卓永强译嘉木央·久麦旺波(1728-179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陈庆英和马连龙译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等6部藏文经典传记文本。总体而言,以上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均得到相关学术机构支持,而学术机构作为翻译赞助者不仅为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出版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也对译者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后期从事藏文传记文学汉译者明显增多,其中大多为学术机构和文化机构工作人员,他们翻译了一批藏文传记文学经典作品,代表性译著有多识·洛桑图丹琼排译热·益西桑格(约12世纪)《大威德之光:密宗大师热罗多吉扎奇异一生》,洛珠加措和俄东瓦拉译雅尔杰·尔金林巴(1323-?)《莲花生传略》与雅尔杰·尔金林巴掘藏本益西措杰(约8世纪)撰《莲花生大师本生传》,张天锁译查同杰布(1452-1507)《玛尔巴译师传》,张新安译嘎玛·弥觉多吉(1507-1559)《日琼巴师徒简传》,德庆卓嘎和张学仁译久美德庆(1540-1615)《汤东杰布传》,汤池安译多卡夏仲·策仁旺杰(1697-1763)《颇罗鼐传》,李风珍节译多喀夏仲·才仁旺杰《颇罗鼐传》,周秋有和李风珍分别译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噶伦传》,汤池安译多仁·丹津班珠尔(1721-1792)《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事》,庄晶译阿旺伦珠达吉(约18世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杨世宏译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1728-1791)《第一世嘉木样传》,克珠群培译直贡·丹增白玛坚参(1770—1826)《直贡法嗣》,郭和卿译法王周加巷(约19世纪)《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戴作民译白玛曲批(约19—20世纪)《释迦牟尼百行传》(又名《白话<如意藤>》),王任邦译才旦夏茸(1910-1985)《宗喀巴大师传记涓滴——敬信开门》,尼玛太译才旦夏茸《喇勤·贡巴饶赛传略》,吴均和谢佐分别译屈焕(又名屈焕嘉措)(1932-)《喜饶嘉措大师传略》等。另外,20世纪90年代杨贵明(拉科·益西多杰)和马吉祥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其中涉及173位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生平事迹[16]。从上述传记选目可以看出,此时翻译文本涉及宁玛、噶举、格鲁等藏传佛教各教派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同时也包括西藏贵族人物传记,可以说,20世纪后期藏文传记文学翻译选材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其中有些译本至今仍是汉语界唯一全译本,其意义不言而喻。
总之,20世纪后期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复苏和发展,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出现高潮,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一辈翻译家在原先译本基础上对译作进行修订,形成了新版本。比如,刘立千和王沂暖的《米拉日巴传》、王尧和陈践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经典译作都是译者在此前译文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的最终版本;二是新时期藏学学术场域促使更多藏汉译者加入到了藏文传记文学的翻译队伍当中,而从译者翻译选材和翻译目的而言,他们不仅看重藏文传记作品的文学价值,更看重其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所以,此时藏文传记文学译著数量显著增多,选目涉及藏文传记文学经典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这些传记文学作品的汉译,极大地满足了国内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需求,也给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
四、21世纪以来藏学与藏文传记文学汉译
21世纪以来中国藏学研究进入稳步繁荣期,此时藏文传记文学汉译无论翻译选材,还是翻译策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继往开来,P.T.1287号《吐蕃赞普传》文献译注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其中大多为前人译本的重新校订和再解读。比如,黄布凡和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任小波《赞普葬礼的先例与吐蕃王政的起源——敦煌P.T.1287号<吐蕃赞普传记>第1节新探》《吐蕃盟歌的文学情味与政治意趣——敦煌P.T.1287号<吐蕃赞普传记>第5、8节探析》,扎巴《赤德颂道歌研究》,朱丽双《赞蒙赛玛噶之歌》《赞普墀松德赞之勋绩——P.T.1287第10节译释》《历史与记忆:P.T.1287第15节新探》等论著都涉及P.T.1287号文献的翻译,而且这些文本对前人译本加以分析、阐释和补正,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样态。其次,早期藏文传记文学文本发掘、翻译与研究方面有了新突破。例如,才让翻译并解读P.T.849号《印度高僧德瓦布扎事略》和P.T.996号《堪布善知识南喀宁布善知识传承略说》两部敦煌藏文写卷为吐蕃佛教人物传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野。
21世纪以来藏传佛教高僧传汉译呈现繁荣发展局面,其中历代达赖喇嘛传记汉译更是取得丰硕成果。在历代达赖喇嘛传记集中汉译活动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承担多卷本《西藏通史》编写课题时组织人员翻译了部分历代达赖喇嘛传记,其中包括陈庆英译比丘益希孜莫(1433-?)《遍知一切之上师根敦珠巴贝桑布传·奇异宝串》、比丘贡噶坚赞(1432-1506)《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十二功业》、根敦嘉措(1476-1542)《二世达赖喇嘛传》,冯智译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图丹晋麦嘉措(1778-1891)《八世达赖喇嘛传》,王维强译第穆·图丹晋美嘉措《九世达赖喇嘛传》,熊文彬译普布觉活佛洛桑楚臣强巴嘉措(1825-1901)《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这6部传记文本与20世纪末所翻译的几部达赖喇嘛传记一同构成“历辈达赖喇嘛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性套书”,成为研究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格鲁派教法史、明清时期西藏地方史、汉满蒙藏民族关系史等领域的基础材料,陈庆英等人也以此为基础撰写出《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一书。可见,21世纪初历代达赖喇嘛藏文传记系统性汉译活动中,作为翻译赞助者的学术机构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华锐·罗桑嘉措译阿旺伦珠达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罗旦译罗桑·赤烈朗杰(约19世纪)《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传》,这两部传记文本作为历代达赖喇嘛传记的组成部分同样丰富了民族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除上述历代达赖喇嘛传记外,藏传佛教高僧传汉译本还有张长虹译吉唐巴·益西贝(约11世纪)《大译师仁钦桑波传》,徐华兰译萨迦·索南孜摩(1142-1182)《巴哩译师传记》,曲甘·完玛多杰译益希辛格(约12世纪)《猛厉火消雪:热·多杰札巴译师传》,仲布·次仁多杰和次朗译觉姆曼姆(1248-1283)掘藏本玉扎宁布(约8世纪)等撰《贝若遮那:一位吐蕃奇僧的传记》,马维光和刘洪记译恰译师曲吉贝(约13世纪)口述并由其弟子曲白达江(约13世纪)笔录《十三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黄颢节译索南维色(约13世纪)《竹钦邬坚巴传》,彭毛多杰译强僧嘉瓦益西(1247-1320)《觉囊派历代传承上师略传》,色让准译衮邦·曲扎贝(1283-1363)《笃布巴·西饶坚赞传记》(又名《遍知法主殊胜本生传》),孔秋加真译多杰泽悟(约14世纪)《噶举金鬘传承上师》,项智多杰等译古格·扎巴坚赞(约15世纪)《拉喇嘛益西沃广传》,释寂凡译乳毕坚谨《米拉日巴传》和郭仓日巴(1494-1570)《热穹巴传记》,卓尕次力和尕藏加洋译班旦·吉美邦(约15世纪)《博东班钦传·善妙喜宴》,徐丽华节译达夏多吉(1655-?)掘藏本南喀宁布(约8世纪)撰《益西措杰传》(全名《吐蕃王妃益西措杰本生传记·示密多弦妙音歌鬘》),钦则·阿旺索巴嘉措译胜怙云增·益希坚参(1713-1793)《菩提道次第师承传》,徐长菊译土观·洛桑曲吉尼玛《第二世土观阿旺曲吉嘉措传》,徐长菊和李梦馨译土观·洛桑曲吉尼玛《大喇嘛菩萨·贡巴饶赛略传·大宝鬘》,曲甘·完玛多杰译察哈尔·罗桑次成(1740-1810)《宗喀巴大师全传》,冯智译扎巴克珠(约18-19世纪)《第65任甘丹赤巴根敦楚臣传》和八世司徒·曲吉琼乃(1699-1774)《八世司徒自传》(选译),张炜明译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0)《蒋扬钦哲旺波传》,堪布格日泽旺译益西多吉(约19世纪)《白玛灯登尊者传》(又名《有缘欢喜甘露云集》),吴均译噶桑勒协(约19-20世纪)《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克珠群培译休色吉尊仁增曲尼桑姆(1853-1951)《休色吉尊仁增曲尼桑姆传》,扎西才旦译拉仁巴格桑嘉措(1899-1990)《至尊喜饶嘉措大师传·圆满妙道之巅》,华热·索南才让译毛尔盖·桑木旦(1913-1993)《毛尔盖·桑木旦自传》,罗桑旦增译霍康·索朗边巴(1919-1995)《根敦群培大师传·清净显相》,张炜明和曲南嘉尊译嘉央洛萨桑博(1919-1993)《大成就者嘉央洛萨桑博自传·善缘耳之喜宴》,蒲文成译屈焕嘉措《导师大格西喜绕嘉措大师事迹简述》,苏得华等译赛仓·罗桑华丹(1937-2021)《藏族历史文化名人传》,华热·索南才让译索南尖参(1968-)《夏日东大师传略》等。另外,一些藏文佛陀传记和印度高僧传记也被译为汉文。例如,智学法师译冈波巴(1079-1153)《帝洛、那若传》,丹增拉巴译娘·尼玛维色(1124-1192)掘藏本益西措杰撰《莲花生传》(又名《莲花生大师传·铜洲版》),杨亿祖编译《金刚歌:八十四尊者传》,达多译格桑曲吉嘉措(约15世纪)《释迦牟尼大传》(全名《无误讲述佛陀出有坏美妙绝伦传记·善逝圣行宝藏》)等。可以说,21世纪以来随着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藏文传记文学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高潮,这一点仅从以上译作数量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藏文传记文学汉译选材多样、内容丰富,昭示着藏文传记文学汉译事业步入深化和拓展的重要阶段,其特征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从翻译人员构成而言,藏文传记文学译研队伍不断壮大,其中既有从事藏学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也有藏传佛教僧侣和信徒,他们也因各自翻译观念与翻译目的的不同使译文各具特色,而且更多藏族译者参与到了翻译实践当中,体现出他们促进藏族文化更真实地走向汉语世界的诉求。第二,从翻译策略和方法而言,藏文传记文学史料价值更加突显,学者型译者更倾向于采用文献研究的翻译方法,其中不仅有文本对勘,而且译者们将藏文传记文学文本放置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诠释和阐发,使译本带有浓厚学术色彩。与此相比,宗教信徒翻译注重宗派传承、师承关系以及文化交流,译本通俗流畅。第三,从翻译选目而言,古代藏传佛教人物传记数量显著增多,敦煌藏文传记文献和现代藏传佛教高僧传记也有拓展。第四,从翻译运行模式而言,学术机构和文化机构作为翻译赞助者依旧起到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相关组织机构的学术眼光,满足了国内学界对藏学资源的需求。总之,21世纪以来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在翻译选材、翻译观念、翻译策略与方法等方面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无论是早期敦煌藏文历史文书的翻译,还是藏传佛教高僧传的翻译都在客观上拓展了人们对藏文传记文学的认识思路,为藏学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结语
藏文传记文学是藏文典籍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数量众多、类型各异,而且文本除浓郁的文学特征外,还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鲜明的民族性,是研究藏族宗教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重要资料。回顾近百年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藏文传记文学汉译是近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诸多译本的产生与流传都与不同时期藏学场域特点密切相关,而且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作为从事藏学研究的译者们不仅翻译正文,而且还以序言、注释、评述、译后记等副文本为译本增值,在推进民族文化交流和藏学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此外,随着藏文传记文学汉译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出现了经典文本的复译现象,反映出翻译的多样性实践特征。总之,近百年历程中藏文传记文学汉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已然成为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学术基础。
参考文献:
[1]法尊.法尊法师自述[J].法音,1985(6):35.
[2]韩敬山.欧阳无畏涉藏经历及藏学研究年表[J].中国藏学,2023(3):192.
[3]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166.
[4]乳毕坚金.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M].王沂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3.
[5][14]桑杰坚赞.米拉日巴传[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24,224.
[6]何峰.从《宗喀巴大师传略十七颂》看道帷格西对宗喀巴精神的弘扬[J].西藏研究,2018(6):32.
[7]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95.
[8]李正栓,王心.民族典籍翻译70年[J].民族翻译,2019(3):9.
[9]阿旺伦珠达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秘传[M].庄晶,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0.
[10]王启龙,阴海燕.中国藏学史(1950—20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1.
[11]王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
[12]黄颢.中国关于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的研究[G]//杨岭多吉主编.四川藏学研究(四),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410—411.
[13]郑堆.70年来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及特点[J],中国藏学,2019(4):24.
[15]陈庆英.我在塔尔寺的经历[G]//杨晓纯,宋颖编.意树心花:文化学者的高原故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21.
[16]藏传佛教高僧传略[M].杨贵明,马吉祥,编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393.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5ZDB082
作者简介:增宝当周(1988-),男,藏族,青海同仁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总第159期)(责编:周晓艳),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