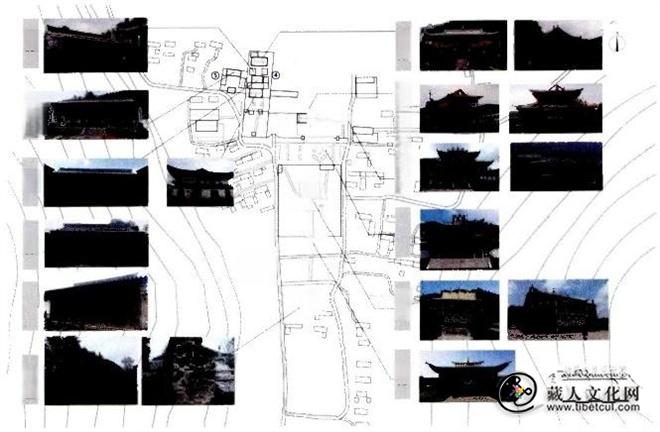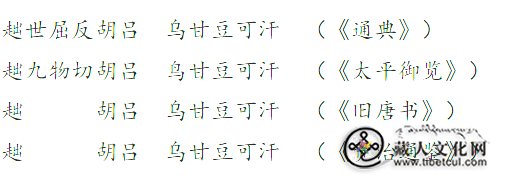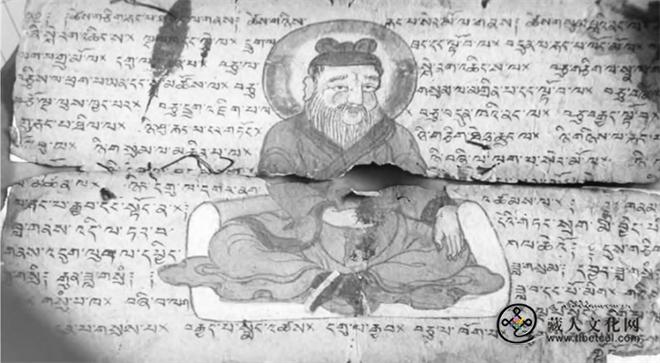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青藏高原从新石器至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时段、不同人群、多样化的迁徙、交流、扩散路线,且彼此之间存在联系与演变关系。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和考古证据的梳理,深入探讨了青藏高原交流路线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研究发现,高原的生业模式直接影响着人类交流模式,从新石器时期分散的粟作农业区域串联起稳定的交流路线,到青铜时期对高海拔区域的开拓,再到历史时期对高原的全面开发,交流路线呈现出逐步稳定和扩展的趋势。研究还表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业模式的改变与跨大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强化密切相关。从交流强度和范围来看,新石器时期至历史时期,青藏高原的交流路线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变,尤其是青铜时期至历史时期,内外部交流全面加强,形成了复杂的交流网络。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青藏高原独特的文化景观,以及其在亚欧文化交流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也能从历史性的演化规律中,进一步把握青藏高原在亚欧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
关键词:青藏高原;交流路线;形成原因
青藏高原处于亚欧大陆早期东方、西方、北方三大文化圈交汇的重要区域,在亚欧文明的交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史前开始的物质、技术、文化交流,形成了青藏高原独特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交汇融合地带。由于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极端而严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活动,所以通常认为在高原很难形成交流路线。研究表明,仰韶中晚期(距今6000—5000年)粟黍种植者沿黄河向西扩张,距今5200年传播至河湟地区,距今5000年到达贵德盆地,最迟距今4500年传播至共和盆地。距今5300年马家窑文化类型为代表的人群自东向西的文化拓展和渗透的路线被学者命名为“彩陶之路”。距今4000年左右大麦和小麦通过欧亚草原—新疆—河西走廊的通道传入高原。西藏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粟黍和麦类作物遗存,是克什米尔地区的麦类和高原东北部的粟黍传播至此。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沿河西走廊至青藏高原东北部。具有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礼器向西传播至民和喇家、广河齐家坪遗址等,并形成了以新疆和田为起点的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历史时期的汉朝形成了以河湟地区为核心西向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联通新疆;东北部沿祁连山脉联通河西走廊;东向与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交流的“羌中道”。小邦部落联盟时期,高原中西部的部落之间交流频繁,雅隆地区的冶炼技术是雅鲁藏布江南北两岸文化交流的结果,而阿里发掘的故如甲木出土了有王侯字样的丝制品和茶叶也证明了青藏高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吐蕃王朝为加强交流开辟了连接中原的“唐蕃古道”,西连中亚的“吐蕃至于阗道”“勃律道”,南接南亚的“尼婆罗道”等多条线路,同时还建立了以西宁为中心,北上张掖,东通兰州至唐王朝,向西通过唐蕃古道连接拉萨的交通邮驿系统。唃斯啰政权统治下的河湟地区成为宋王朝与西域商贸的枢纽。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交通驿站。明朝修建“官道”。“茶马古道”连接和沟通川、滇、藏三地,使其成为这一时期高原最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交流路线。
由此可知,青藏高原从新石器至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时段、不同人群、多样化的迁徙、交流、扩散路线,且前后、彼此之间存在联系与演变关系,既往研究主要基于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记载描述交流的具体路线,尚未系统探讨青藏高原从新石器至历史时期交流路线形成、发展、演变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高原交流路线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认识。在梳理现有的研究资料和考古证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高原从新石器时期至历史时期交流路线形成的原因,以期对高原交流路线的详细演进过程有进一步认识。
一、农业生业模式下交流路线的形成
仰韶文化(距今7000—6000年)出土的粟黍遗存占比较高,显示出粟黍种植在生业模式中的比重较高。到仰韶中晚期,粟黍农作物开始沿黄河扩张至黄河上游地区,在距今5200年传播至河湟谷地,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距今5500—5300年),发现少量的粟黍炭化种子。距今5000—4500年粟黍农作物继续向西扩张到河西走廊地区,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距今4900—4000年)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粟黍。在高原共和—贵德盆地的宗日文化(距今5200—4100年)C、N同位素研究显示,其发展经历了农业与狩猎采集的混和经济模式向稳定农业转变的过程。半山—马场时期(距今4500—4000年)时期河湟地区的先民以C4食物为主,柳湾遗址出现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如石斧、石刀、石镰等。西藏昌都卡若遗存中发现了粟黍遗存,西藏的昌果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黍的植物遗存。卡若文化或类似遗存在西藏当雄、林芝、墨脱,印度锡金邦北部均有发现。
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公元前475-公元8年)麦类作物才成为青海东部地区主要的食物来源。在西藏的昌果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黍和麦类作物的植物遗存,拉萨曲贡遗址(距今4000—3500年)中有大量用于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说明了曲贡人的农业生产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经济生产门类,西藏乃东邦嘎遗址和昌都小恩达遗址中有房屋居址,很可能是有规模的定居农业形成的聚落。西藏西札达县境内的丁东遗址(距今2400—1900年)发现经鉴定为青稞的碳化植物遗存,这是西藏西部首次发现的史前人工栽培青稞作物的证据。来自全基因组捕获的数据显示,大麦大约在距今4500—3500年,通过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引入我国西藏南部。以上考古证据显示青铜时期,麦类取代粟黍成为高原高海拔地区史前人类利用的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青藏高原东北部人骨同位素的证据也证明,同位素值呈现以C3作物(主要是大麦)为主的食物来源,麦作农业成为东北部定居高原的古人类选择的生存战略,并促使人类永久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粟黍是典型的喜温、耐旱作物,生长期要求的≥10℃积温在1600℃-3000℃,一般的温度下限为10℃,生长环境最合适的温度为15℃-25℃,年均温5℃-10℃,粟的产量较高,适宜降水量450-550毫米的环境,黍具有更强的耐旱性,降水350-450毫米的环境中也能生存,所以在高原分布的范围更广,粟黍农业对水热和霜冻的敏感反应使其无法在海拔2500m以上的区域存活。小麦种植需要的适宜温度约在10℃-15℃,青稞是喜凉作物,≥0℃有效积温达到1200℃-1500℃就可以满足种植条件,所以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约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43%。
青藏高原适宜这一物候条件的区域有:黄河、湟水及洮河河谷地带,气候属于高原温带半干旱气候,最暖月均温约12℃-18℃,年降水量大约为300-600毫米,水热资源较丰富;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受到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暖湿气候的影响,具有湿润、半湿润的气候特征,年降水量500-1000毫米,适宜农业种植;藏南谷地受地形影响显著,期间的宽谷盆地最暖月均温10℃-16℃,年降水量大约为300-500毫米,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下游谷地,至今都是西藏最重要的农作物产区;青藏高原的气候具有显著的海拔分异,在海拔2500-4000米的河谷中最暖月均温在12℃-18℃;而海拔4000-4500米的高原面和高山上则在6℃-10℃之间。
青藏高原早期的交流路线也正好印证了高原物候条件适宜粟黍农业生产的区域,这一区域内的≥10℃积温正好为1600℃-3000℃,处于400-600毫米等降水线以内(图1),这些区域是发展粟作农业的理想之地,这些分散的小型农业基地成为串联新石器交流路线的基础。青铜时期由边缘向腹地延伸的交流路线,正好位于≥0℃积温在1000℃-1500℃,等降水线300-400毫米区域内,该区域内适宜耐寒耐旱的麦类作物种植,所以青铜时期麦类作物向高海拔地区的扩张使得交流路线也向腹地扩张。
二、农牧业并重的生业模式下交流路线的形成
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青海和西藏来说,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大约为可利用土地的10%,而且受地形、水源、气候的强烈影响。青海除了河湟东部地区和河谷地带有零星农业分布外,其余地区均是纯牧区,尤其是青南的大部分地区最暖月的均温约6℃-10℃,植物生长期很短,仅为90-100天,不适合发展农业,但是该地区分布着较大面积的草原植被资源,其中以紫花针茅(Stipapupurea)为主的高寒草原和以丝颖针茅(Stipacapillacea)为主组成的高寒草甸草原为主,是放牧牦牛和绵羊为主的纯牧区。高原西部的羌塘高原气候寒冷,最冷月均温在-10℃以下;冬春多大风;植被主要由紫花针茅(Stipapurpurea)为主组成的高寒草原,也是以放牧为主的牧区,羌塘北部尚有相当面积的“无人区”是野牦牛、藏羚和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家园。
从考古证据来看,位于藏北高原青铜晚期的当雄加日塘遗址(距今3000—公元7世纪左右)出土大量细石器,说明游猎的生业模式在西藏高原一直延续到青铜晚期,目前西藏高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材料所能观察到的经济模式,一种是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农—牧业兼营的青铜早期经济类型;另一种是以加日塘为代表的游牧—猎兼营的游牧青铜晚期经济类型。青海地区分布在大通河和湟水河流域以及青海湖盆地的卡约文化(距今3600—2600年)中期便已出现了专业化的游牧经济,卡约文化分布在2500—3200米海拔区域,卡约文化中的阿哈特拉墓地类型、湟源县的莫布拉遗址、大华中庄卡约墓地早期的殉猪习俗在晚期几乎全部以马、牛、羊代替,这种变化反映了高原东北部由混合农业向游牧的转变。青铜时期的诺木洪文化(距今3400—2700年)分布在≥2800米以上的区域,主要从事麦类种植、牧羊和牦牛的混合生产方式,这一分布格局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在不同海拔区间内已经出现了农牧业各自发展的生业模式。
通过牦牛全基因组测序揭示出,青藏高原驯化牦牛的时间为距今7300年,牦牛的驯化除了食肉还可以获取燃料(牛粪)、牛奶、奶酪、皮毛等的二次产品,一般不会用于农耕;而且牦牛驯养可能发生在全新世中期农牧相结合的区域,比如说宗日文化。青海湖盆地的早期放牧出现在距今6000—5500年间;研究同时推测最初人类是跟随野牦牛的迁徙路线进入藏北高原,全新世人类是为了放牧向青藏高山草原地区迁居,这说明至少在全新世中期,高原的部分地区已经有了驯化牦牛和开展畜牧活动的迹象。
宗日遗址中发现海贝,在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广泛发现,可能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是农牧区存在广泛贸易与交流的有力佐证,这说明大约距今5000年高原东部就可能存在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种植者之间的贸易与交换,这一贸易和交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青铜时期得以强化,并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在《唐会要》第99卷中对吐蕃部落时期大羊同的记载中有“辫发毡裘,畜牧为业”的记载,《隋书》第83卷记载苏毗部落“气候多寒,射猎为业”,吐蕃王朝建立后农业经济也仅集中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河谷地带,藏北、羌塘、甘青地区的羌、氐游牧文化依然是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同时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中,记载了土地“蕃租”是当时吐蕃人对其扩张至宜农区域采取的策略,这一策略侧面反映出吐蕃人不适农业而对畜牧经济的倾向。
以上证据表明,除了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外,高原大部分地区更适合发展游牧业经济,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高原的细石器狩猎采集人群有可能很早就开始利用高原优质的草场资源驯化动物牦牛,少部分狩猎采集者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就直接转化为游牧者,为了适应高原极端环境采用游动迁徙的策略,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实践后,有可能就变成了随季节变化根据不同的海拔高度进行冬夏牧场转场,从而使动物在冬、夏都能利用高原的草场植被资源,青铜时期驯化动物羊、马的传入使得游牧业得以快速发展。农业和牧业经济自身的互补性,使得农牧业混合经济的交错地带具有交流或者贸易频繁的特点。
总之,独特的自然环境使高原的主体经济模式一直以游牧业为主,兼有河谷农业,而且游牧活动的范围大概发生在海拔≥3600米的区域内,而海拔2600-3600米则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的农牧业混合交错地带,海拔≤2600米的区域则是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区域(图2)。所以除了农业种植区外,农牧混合带也极易形成稳定的交流路线,而且农业人群与游牧人群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在形成稳定路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交流从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在青铜时期得到强化,并在历史时期得到发展。
三、交流强化模式下交流路线的形成
从新石器至历史时期的交流路线来看,高原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形成了两个明显的路线密集区。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就形成密集路线区,这与仰韶文化传入东北部有关,至青铜时期东北部经历了齐家、卡约、辛店文化形态,使其一直处于文化集聚热点区,这与东北部持续受到来自黄土高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同时从西亚和中亚沿新疆—河西走廊长线传播至此的麦类、驯化羊马、青铜冶金技术等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考古学者在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遗址的挖掘中发现了具有仰韶文化彩陶特征的花瓣纹与三角纹,以及马家窑出土的具有南亚风格的串珠都进一步证明,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东北部已经有一条长线传播路线与南亚互动交流,这一互动交流的路线是高原东北部的文化因素沿着东部—东南—雅鲁藏布江传播,具体来看是仰韶文化—南亚沿雅鲁藏布江的长线互动交流。青铜时期通过吉隆和普兰河谷跨喜马拉雅山脉进入雅鲁藏布江南岸的交流互动,使得高原西南地区的拉萨河谷地区也形成了相对较密集的交流路线区。历史时期,高原的东北部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联系加强,西南部则通过增加的亚东和樟木两个河谷加强了跨越喜马拉雅山脉与南亚的交流,高原西北部通过经新疆与“丝绸之路”相连加强了与西亚、中亚的交流,历史时期重要的商贸路线“茶马古道”加强了青藏与川滇的交流互动,高原腹地形成的“唐蕃古道”又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结,所以直至历史时期高原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复杂的高原交流路网。
四、聚落—战争因素主导模式下交流路线的形成
官亭盆地、乐都盆地和西宁盆地在马家窑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和辛店文化时期聚落结构发展较好,古人类在选择稳定定居聚落时会充分考虑其功能使用的便捷性与资源利用的便宜性,新石器—青铜时期从聚落与海拔的关系来看,聚落所在的平均海拔整体较低,到辛店文化时期聚落有向高海拔迁移的趋势,但低地依然保留有一定的聚落。从聚落与河流的关系来看马家窑文化早中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晚期则转移至湟水谷地,青铜时期的聚落又集中分布在黄河上游谷地及其支流。
从历史时期遗址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吐蕃王朝时期的遗址点在高原东北部和西南部均形成了一个集聚分布的区域,元代高原上遗址数量相比吐蕃王朝虽然有所下降,降幅达72.46%,但相对集中的遗址点还是分布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明代遗址点中有59.54%的遗址点位于海拔3000米以下的河谷盆地,从分布范围来看,自明代起遗址在河湟谷地、四川北部横断山谷地、雅鲁藏布江谷地形成明显的“核心区”,但整体上呈现出沿东北—东部—东南—西南月牙形分布的特点,这一分布格局大致能反映出历史时期人类活动较密集的区域。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秦汉时期青藏高原东北部是古羌人活动的范围,通过文献记载学者认为羌人已经从事专业化的具有稳定居址的游牧业了。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从秦人那里学到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大型定居农业经济的出现,推动了羌人社会生产的发展。随着与青藏高原毗邻的关中平原中央集权的逐步设置,经历了秦、汉的历史发展,中央王朝对河湟地区设郡建置,通过移民和屯田政策,大力发展农业;西汉末年,王莽政权在青海湖的东部今海北州海晏县设置了西海郡,以规模农业生产为经济支柱的高原聚落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聚落形成后,羌人与中原联系加强,同时也促进了交流道路的开辟。
青藏高原的中西部,藏南河谷的雅砻部落具有较发达的农业经济,为日后统一其他部落提供了经济条件,高原的各个部落之间存在商业贸易。随着聚落的不断壮大和加强,至吐蕃王朝建立之后,以拉萨河谷为中心建立了以聚落为核心,辐射整个高原的交通邮驿体系。
到元明清时期,青藏高原有了固定的交通驿站,明《寰宇通衢》中记载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的民和—乐都—平安—西宁的一线有7个驿站,西藏境内主要以拉萨为中心的7个驿站,以日喀则为中心有4个大型的驿站,到清朝,民和—西宁—湟源、西宁—大通有固定的驿站18个(杨应琚,清)。
中原与高原的贸易也是通过固定的聚落来实现的,稳定的聚落是茶马互市主要的交易地点,隋唐时期的承风岭(今贵德千户附近),北宋初年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明朝指定在湟中县境内的镇海堡进行互市,并进一步设置了“安定”“曲先”“阿端”“罕东”“沙州”“赤斤”“哈密”七卫,加强哈密以东—嘉峪关以西—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的贸易交易;清朝初年,互市地点移至今湟中区多巴镇。
除此之外,民族迁徙、战争也在路线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朝为开拓疆土,迫使黄土高原西部戎人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羌人向高原东南部迁徙。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中,出土有大量的兵器,其中的汉代木简中记载了当时的功爵、等级制度和征战功绩、赏赐以及军队的编制、旗帜、作战部署兵车配备、弓矢和弩的使用,等等。汉朝将军赵充国平羌时,中郎将赵卬与金城(今兰州市)太守共同防御祁连山间的羌人,共同维护河湟羌人与河西地区的物资供应,形成了沿乐都北上武威,南下金城的路线。青海湖西北地区的罕开羌在秋收后要攻击当时的酒泉和敦煌二郡,郡守辛武贤率部南下,深入八百里到达青海湖以北的祁连山,与赵充国统兵西进,共同合击罕开羌,形成了一条由鲜水(青海湖)至酒泉的路线。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安夷县的一个官吏,因强占卑湳羌人妻子被杀,县令宗延率兵追讨,卑湳羌人反抗,陇西太守孙纯派遣李睦出塞讨伐,双方会战于和罗谷(即化隆谷,今化隆昂思多沟),卑湳羌战败,卑湳羌原来居住于大小榆谷(共和盆地的贵德至尖扎黄河以南的河谷),因为烧当羌兴起而移居黄河以北,因这次战败遂向黄河上游移居,逐渐融合发展成后来的白兰羌。据史载,北魏、吐谷浑、吐蕃、唐朝军队在共和盆地爆发了多次战争。历史时期农牧业的全面发展致使稳定的聚落产生,功能齐全且稳定的聚落为人类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历史时期稳定聚落为核心节点的交流路线,并在政治、战争、商业贸易等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路网形态。
结语
青藏高原早期交流路线完整呈现了青藏高原新石器—历史时期人类复杂的互动交流,最终结果是形成高原复杂的交流路线,同时反映出的是人类对环境、生产方式以及互动交流强度对高原的逐步适应过程。
从地形地貌来看,高原独特的地形地貌影响路线的走向,青藏高原除东北部没有高大山脉阻隔,四周分布的高大山脉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较大的海拔高差,复杂的地形条件,明显的气候差异,增强了高原与周邻地区的交流通行难度,但高大山脉间分布的山间盆地和宽谷成为交流的理想通道。具体来看,东北部形成一个通往高原内部的天然通道,使黄河上游仰韶文化通过这一通道进入高原;高原北部祁连山分布的纵向宽谷形成了由北部进入高原的路线;高原西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向的交流通过普兰、吉隆、樟木、亚东为主的山口河谷区域进行交流;高原西北部的北昆仑山和南喀喇昆仑山之间、昆仑山和岗底斯山脉之间,广泛分布着东西向的山间盆地和宽谷成为西向进入高原的理想通道;高原腹地区南北向的交通在自西向东横亘的高大山脉的阻隔下通行不易,但是东西向的交流相对较通畅。柴达木盆地作为一个封闭的内陆高原盆地,受干旱气候条件影响,横穿柴达木盆地内部的路线基本上不存在,而沿着盆地边缘的绿洲地区则形成了由北部进入高原的路线。
从气候环境来看,新石器时期,在相对适宜的环境和人口增值压力的背景下,以粟黍农业种植为主的仰韶文化进入高原,粟作农业者沿着河湟谷地—澜沧江长江流域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传播,而该区域物候正好适宜粟黍农业种植,说明新石器相对适宜的气候环境和粟作农业的传播种植是路线形成的基础。青铜时期,在干冷的气候条件下,原有的粟作农业种植经济受到挑战,但随着跨大陆麦类作物、驯化羊、马的传入,使得农、牧业经济得到发展,表现在农业种植向高海拔种植区开拓,出现高海拔游牧经济,这导致人类活动向高海拔区域延伸;同时在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混合交错地带,文化交流及贸易行为加强。历史时期,尽管也伴随着气候波动,但农业产品的多元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功能齐全且稳定的聚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基础,人类突破自然限制的能力较前期大大提升,人口数量增加,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
从生业模式来看,高原不同的生业模式直接影响高原早期人类交流模式,使其发展的过程呈现出对高原资源的简单索取—发展至新石器时期分散的小型粟作农业区域首先串联起稳定的路线—青铜时期对高海拔区域的开拓—历史时期对高原主动全面开发利用的交流模式。在生业模式和交流模式的共同影响下,高原早期路线经历了新石器时期农业定居区首先形成稳定的路线;青铜时期的农、牧业混合交界带形成了稳定路线;历史时期稳定的路线在聚落间形成的发展模式。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业模式的改变与跨大陆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强化有关。
从交流强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交流互动是仰韶文化通过高原南部边缘对川西、云南等地的影响,并沿雅鲁藏布江与南亚的互动交流,发展至青铜时由中亚—沿新疆—河西走廊至高原北缘的互动交流加强,历史时期则是南、北边缘的交流不断强化,伴随着与中原王朝对该地区复杂的政治、文化互动,以及商业贸易的强有力刺激,内外部交流全面加强的结果。
作者简介:兰措卓玛,青海大学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全球变化与人类响应。侯光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
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