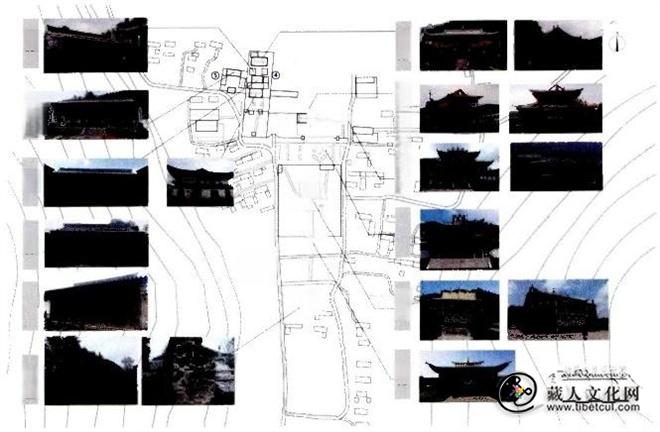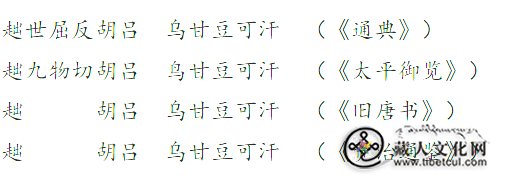摄影:曾晓鸿
摄影:曾晓鸿
摘要: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甘青地区;藏传佛教
特定的地理环境既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基础,也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与宗教范围。藏传佛教是青藏高原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甘青地区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流布区域,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
一、甘青地区自然环境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地理环境和宗教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宗教的传播途径与分布特征;另一方面,宗教起源于自然压迫,宗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宗教必然影响人们改变地理环境的程度”[1]。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我们不能离开地理环境来研究人类文化,人类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不同文化创造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也是如此。青海大部和甘南地区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传佛教发展、流布的主要地区。甘肃省内其余地区是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与之间的过渡地带,受到藏传佛教的辐射和影响,也有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
藏传佛教是佛教三大语系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以后吸收吐蕃民族的原始信仰“苯教”诸多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从佛教发展史上看,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后期发展的产物,起源于公元四世纪,形成于公元八九世纪,成熟于十二三世纪,带有鲜明的佛教中晚期的文化印迹。” [2]1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以后在这一地区经过本土化改造后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其与高原早期已有的宗教(包括苯教及一些原始宗教)的斗争、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在与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的斗争、融合中,藏传佛教才得以形成、确立,因而藏传佛教也带有许多高原早期宗教的烙印。”[3]170吐蕃民族早期信仰的苯教是一种典型的泛神论宗教,万物有灵观念根深蒂固。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能力有限,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将各种自然造物人格化,造就了难以计数的神灵。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不一而足。周边环境中神灵无处不在,万物都有自己的灵魂。宗教是对客观世界一种虚幻的认识,宗教意识源于环境和社会的压迫。吐蕃先民的生产、生活依赖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受到这里严酷自然环境的巨大压迫。
青藏高原地势高峻,其气候条件与同纬度的低海拔地区差异非常明显,“因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动力作用、下垫面差异以及山脉地形对风、降水、冷空气灭气影响,形成独特的高原气候特点,同时深刻制约着生态系统的发育。”[4]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干寒,降雨稀少,绝大多数地区的气候以寒冷干燥为主。仅有一些海拔较低的河谷、湖泊周围,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具备农业耕作所需要的水热条件。青藏高原的南缘地带的雅鲁藏布江河谷、东南边缘地带的横断山区受绝对高差显著,气候带垂直分布非常明显。“大抵一县之中,附近河谷平原之地气候最为温暖,有时较内地尤热;低山部分,温和;高山则渐凉爽,至达四千七八百米以上之山岭,则百物不生,人迹罕至,雪海冰川而已。”[5]77《唐会要》中记载这里的气候状况,“其地风雨雷电,每隔日有之,盛夏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6]1729其他汉、藏文史籍中也频繁出现,“少暑多寒,且寒暑变迁甚剧”[7]158-159,“多霆、电、风、雹、积雪……山谷常冰”[8]2072等记载。可见,多寒少暑、冬长无夏是这一地区最为典型的气候特征,只是在海拔高度不同地区其具体表现有一定的差异。
严酷的自然环境限制了青藏高原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畜牧业经济成为高原各民族的必然选择。高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崇拜,较大因素是源于这种环境的压迫。所以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是故西藏者,天然之佛地也。”[9]15也有学者说:“这种喇嘛寺的产生有种种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地理的。”[10]422而藏传佛教之所以在形成过程中将苯教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等因素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体系之中,其根本原因也是地理的,“自然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则后来通过融合也部分地为藏传佛教所继承下来,例如对于高山大湖的敬畏及对白石的崇拜等。而这些并非早期佛教固有的内容,因此可将其视作早期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的影响而间接影响藏传佛教的形成。”[11]170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青藏高原经过本土化改造后成为藏传佛教,并在这里扎下雄厚的根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对宇宙结构的认识论,其六道轮回、普度众生等教义观念和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非常契合。《汉藏史集》描述青藏高原,“南瞻部洲的中心是有雪吐蕃,是因为吐蕃地高、山多、雪山不化,所有河流都是由此向外流出的缘故,故认为它是南瞻部洲之中心”。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以后,“十方诸佛境界中,见圣观自在菩萨承昔愿力,使有雪藏地一切有情皆得成熟解脱,此边地如昏暗处,燃光明灯,变为宝地。”[12]40“三宝慈悲对众生一视同仁,如同阳光普照;护法的感应非常及时,如同大海的波涛;由缘起的力量所欲均能如愿满足,如同如意宝树;这真实不虚的法力,谁发什么愿,一切皆能如愿成就。”[13]245正是契合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才能被这里的民众所接受,才能成为这一地区一种重要的统治思想。
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在甘青地区广泛传播,与吐蕃王朝的东扩及其所带来的藏民族分布区域扩大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时期真正意义的藏传佛教尚未形成,但吐蕃的东扩奠定了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众基础。“随着吐蕃王朝的扩张,在甘肃、青海、四川广大牧业区,则有不少西羌系、鲜卑吐谷浑系的游牧部落被统一到吐蕃的统治之下,逐渐融入藏族之中。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之后,还将其统治下的汉人也编为部落之组织形式,以便管理。”[14]3
雄伟高峻的地势、连绵纵横的群山,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各个民族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生存空间,也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环境束缚。吐蕃王朝崛起于青藏高原以后,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挣脱地理环境对自身发展的束缚,开始了对其周边区域的扩张。而其对外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位于其东北方向的今青海地区。吐蕃王朝位于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这里是中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的最高一级,总体地形构造是西北高、东南低,地势从西北逐渐向东南倾斜。从西北向东南依次是藏北高原、藏南谷地、藏东峡谷区三个地形阶梯,“这种地处东亚地形板块的最西端、面向内地并向内地倾斜的地形构造,使它在地理单元上天然地与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二者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15]吐蕃四境被群山所环峙,其西部、南部是奇雄险峻的喜马拉雅山,北部则是巍巍昆仑山脉自西向东绵延横亘。这两大山系的平均海拔均在6000米以上,成为吐蕃王朝难以逾越的天然地形屏障,遏制了吐蕃势力的扩张。而吐蕃东北部的唐古拉山脉、东部的横断山脉,虽然也形成了山水阻隔,但由于有山间孔道的存在,并不像其他方向那样难以突破,所以成为吐蕃王朝一个主要扩张方向。
吐蕃王朝对于扩张方向的选择,对甘青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其后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
二、民族分布格局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民众是藏传佛教的信仰之基,是藏传佛教发展传播的载体。因此,甘青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是藏传佛教在这里传播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前述对甘青地区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甘青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这里既有广阔的高原草场,又有连绵纵横的山脉,还有适宜农耕的宽阔河谷以及适宜发展绿洲农业的戈壁荒漠。多样的地形地貌以及不同的区域气候条件使这里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不同的民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受地理环境影响,甘青地区人口分布,“一直是东密西疏,很不平衡,并呈阶梯状立体分布。如现阶段,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山和草原地区,人烟稀少,主要分布着从事游牧业的藏族、蒙古族等;半浅山地区主要居住者(定居或半定居)从事牧业的藏族、裕固族等;浅山、河川地区人口稠密,主要居住着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土族、保安族等。”[16]5-6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甘青地区成为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多元文化兼容并立的区域。“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布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藏传佛教跨地区、跨民族的宗教文化传播过程,共同的人文环境及历史因素可产生共同的信仰,而共同的信仰更有助于促进民族间的联系与交往。正是基于这些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明清以来甘青地区兴起了一批具有广泛宗教影响的藏传佛教名刹大寺,成为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各民族信徒朝拜顶礼的信仰中心,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沟通起到了特殊的纽结作用。”[17]204
甘青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处共居的地区,不同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特点,但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中,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熏染。从公元10世纪后弘期以来,在藏民族文化土壤中孕生而成的藏传佛教不仅成为藏族的信仰,而且也普遍传播于同一区域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中,成为这些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并通过共同信仰这一无形的纽带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宗教的印痕。即所谓“牧畜农业,人民所资以为生者,而恒遭造物之摧毁。藏族竭其智能不足以争,于是将所祈求之愿望与要求,寄托于宗教神幻世界,以求于鬼神。”[18]12这些民族的分布区域也就成为藏传佛教在这里的传播的重点区域。
甘青地区藏民族重要的分布地区,青海地区的藏族主要分布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此外西宁、海东地区也有藏族的分布。甘肃的藏族主要分布在“位于甘肃南部草原地带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含七县)和祁连山麓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两地,以及陇南的岷县、宕昌、武都、文县和河西走廊肃南县部分地区。藏族在甘肃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吐蕃王朝时期这里曾被吐蕃军事占领。公元8世纪至14世纪期间,藏族部落还曾一度遍布甘肃各地。”[19]3元代开始,曾遍及西北的吐蕃部落开始收缩到今青海牧区以及甘南草原,形成青海湖周围的“环海八族”聚居区,海北、海西藏族聚居区,甘南草原藏族聚居区。[20]131到清代这些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地方被普遍称为安多地区。
蒙古族在蒙元王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进入甘青地区。公元1239年,蒙古窝阔台大汗之子阔端派其部将朵儿达拉罕等率军经青海地区进入乌思藏。公元1253年,蒙古人又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置了“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到元代初年改称“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安多地区藏族各部的管理。
甘青地区被纳入蒙古的统治范围后,蒙古统治者不断派宗室亲贵出镇这里。西夏和金被蒙古灭亡以后,甘青地区被赐给窝阔台大汗之子阔端作为封地。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划分今甘肃临夏、青海东部地区以及四川北部地区由其进行管理。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中央政府又封章吉附马为宁濮郡王,出镇西宁。蒙古对甘青地区的一系列统治措施使得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进入这里。
蒙古族早期信仰的是萨满教,信仰藏传佛教则开始于蒙元早期,但那时主要局限于蒙古上层阶层之中。公元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在凉州会晤,通过这次会晤,元朝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凉州会谈既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性会晤,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一次重要传法活动。在此期间,萨班贡嘎坚赞“为阔端王及其部属授予喜金刚的灌顶,显示各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21]26有些学者推测,阔端及其部属可能由此开始信奉藏传佛教。
凉州会谈以后,出于对西藏等藏族聚居区进行政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和扶持藏传佛教,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元代是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没有蒙古统治者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蒙元前期,相当数量的蒙古宗王及官、军、民匠等进入甘青地区,在信仰风俗上也必然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明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结盟,标志着东蒙古各部基本都皈信了藏传佛教,甘青地区因此成为藏传佛教向蒙古地区传播的一个过渡性地带。此后,以格鲁派为主的大量藏传佛教高僧经甘青地区并由此到蒙古各地进行传法活动,格鲁派在蒙古各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至公元17世纪30年代,西蒙古和硕特部更以格鲁派“护教者”的身份,从新疆地区举部南下,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并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独尊地位。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也正是在和硕特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清初,和硕特汗国在大一统潮流的冲击下解体,但藏传佛教信仰却早已深深根植于甘青地区蒙古族社会之中。
土族是甘青境内特有的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土族的形成大约是在明代后期。土族的族源,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相关学者的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已由原本的四、五种说法集中于两种看法。也就是在土族族源研究中最具影响的“蒙古说”和“吐谷浑说”。
明清以来,土族所处的河湟地区涌现出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这对土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纷纷建寺立庙,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明朝洪武、永乐时期,担任西宁卫镇抚的土族土官李南哥捐资建成藏传佛教寺院宁番寺和卧佛寺,其中宁番寺的寺额系李南哥奏请明太祖朱元璋亲赐。[22]105据《安多政教史》的记载:明代,甘肃土族鲁土司也修建了数座藏传佛教寺院,并且由其族人出家住持,掌握教权。如大通大寺,就由出身于鲁土司家族的喇嘛喜饶尼玛修建,而主要施主便是鲁土司。当时还有萨迦派喇嘛曲吉坚赞和格鲁派喇嘛鲁本·桑木旦森格曾与鲁土司结为供施关系,在当地修建了5座寺院。[23]127《安多政教史》中还记载今大通境内的金刚持寺,“由鲁嘉阿者黎的历世转世化身和鲁土司供施双方把它和(大通)大寺结合一起共同护理。”[24]128生活在青海同仁地区的土族,更是深受隆务寺的影响,在其聚居的吾屯、郭麻日、年都乎、尕洒日等所谓“四寨子”均建有藏传佛教寺院。位于今互助县的格鲁派大寺佑宁寺,“除了少数之外,其中喇嘛全系土人”[25]68,“藏籍僧侣甚少,住持(清代官书称法台khri-pa)以下僧徒,几尽为土人。清代著名喇嘛如章嘉、土观禅师,亦悉为土人,非番族,寺内通行语言即土语。”[26]211位于今湟中的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该寺院中土族僧人占有相当比例。1954年时塔尔寺共有僧人1759人,其中土族僧人共380多人,占了22%。[27]92此外,拉卜楞寺、广惠寺、却藏寺等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大寺中,土族喇嘛都为数众多。
裕固族先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甘州回鹘、黄头回纥以及元明时期的撒里畏兀儿人。清康熙三十七年(1689),撒里畏兀儿被划分为大头目家、八个家、五个家、罗儿家、亚罗格家以及贺朗格家七个部落,统称为“黄番七族”。裕固族的居地主要在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以及酒泉市黄泥堡等地,始终是与藏族相邻、杂处,受到了藏族宗教与文化的显著影响。明代撒里畏兀儿各部中,就有一些僧人被授予国师、禅师等封号。明正统四年(1439),有安定卫国师赏竹领真“化导部属人等来朝”[28]971,后来其侄摄刺藏卜袭国师名号,明廷令其协同安定王“推广慈教,以化部属。”[29]2466正统九年(1444),命罕东卫僧人端岳监藏袭其叔格剌思巴监藏大国师之号。[30]2477到清代初年,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裕固族各部的普遍信仰,特别是青海佑宁寺、广惠寺以及东科寺在肃南地区影响巨大,这里也逐步建立了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几乎每个部落都建有自己的寺院。据调查,在20世纪50年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还有藏传佛教寺院15座之多。[31]
除上述民族外,甘青地区特别是河、湟、洮、岷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汉族民众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到藏传佛教寺院出家为僧,即所谓“汉人亦有为番僧者。”[32]385如肃南地区的马蹄寺,其原本就是汉传佛教寺院,后来改宗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清代,该寺分为南北两寺,南寺喇嘛全系藏族,北寺喇嘛则全部为汉族。[33]565青海塔尔寺、东科寺等许多寺院中都有汉族男子入寺为僧,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就有数十名汉族喇嘛。[34]
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甘青地区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密切的交融互动关系。甘青地区也由此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信仰为纽带,以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各民族为主体,兼容部分汉族的藏传佛教文化圈。
三、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对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甘青地区和西藏山水相连,是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成为重要的藏族分布地区。也正是这种地理区位特点,使得青海河湟地区成为吐蕃王朝末期西藏佛教受郎达玛灭佛影响而面临消亡时的复兴基地,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祥地。
郎达玛禁佛之时,修行于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曲沃日山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三名僧人辗转来到了青海东部的青海河湟谷地。他们先“居住于今尖扎县城北约40公里处坎布拉林区的阿琼南宗,一度活动于今该县加让乡的洛多杰扎岩等地,后移居今化隆县金源乡境内的丹斗地方,又一度活动于今乐都县中坝乡的央宗坪和今平安、互助等县的湟水谷地。”[35]24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在这些地方潜心修行,传播佛法,由于郎达玛禁佛险遭灭顶之灾的西藏佛教在河湟地区开始复兴。
至10世纪末,随着西藏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各地方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新的统治秩序逐渐确立。佛教也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和得力工具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地方权贵开始迎僧建寺。“970年,西藏山南地区新兴的封建领主、达玛之子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虔信佛教,听说青海丹斗地区有佛法流传,便资助鲁梅楚臣喜饶、热希楚臣迥乃、仲·耶希云丹等来自前藏和后藏的10人(一说7人)到丹斗,从喇钦·贡巴饶赛剃度出家。这些人经过数年勤奋修学,受比丘戒后,约于978年前后陆续返回西藏,在各地新兴封建领主的资助下修建了一批寺院,收徒传教逐渐形成寺院僧团,使藏语系佛教再度恢复发展。”[36]44西藏佛教也进入了的后弘期,并迅速成为了西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佛教在西藏复兴之后,由于教法、教理传承上的差异性,加之当时西藏社会内部政治上的割据,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藏传佛教后弘期初,各佛教流派与称雄一方的封建实力集团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各大宗派。从此,宗派利益与世俗利益混杂不分,它们在争夺‘正统’旗号下的封建割据斗争日益激烈。各宗派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向外发展,寻求新的‘化宇’,于是,藏传佛教文化冲破了内层区域的界限,植根于青藏高原边缘的许多民族中。”[37]4
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之所以能够得以广泛传播,除了坚实的信仰基础以外,历代中央政权的重视与扶持密切相关,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38]178。宗教与民族问题和社会政治有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历代政权的宗教政策均是服务于其社会政治大局,而历代中央政权制定对甘青地区的统治方略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这里特殊的区位。在宗教统治政策上,明清统治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力提升甘青地区藏传佛教上层的宗教地位,借以对西藏地区的宗教势力施以影响。“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羁縻藏族部落,曾在甘青藏传佛教地区推行过多种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政策,如设置番僧僧纲司,采用多封众建办法封赠上层喇嘛,培养驻京呼图克图等。”[39]147
有明一代,对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是采取宗教羁縻和经济笼络相结合的办法强化其内聚力。基于甘青地区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借鉴元的土司制度,采取“以夷治夷”的办法,以少数民族的酋长“世袭罔替”地担任当地的土官,治理本部族民众。同时,又把在汉族地区推行的僧纲司制度加以改造、移植,作为土司制的补充,广泛推行到甘青地区,名曰番僧僧纲司。其目的是选择、培养僧官,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治理以有效控制地方社会。明清时期在甘青地区的僧纲司设置,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甘青的地理区位和民族分布,通过这一办法以稳定地方继而影响西藏。这一点,在清王朝对驻京呼图克图的选择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政府钦定喇嘛班第,确定了12位呼图克图在京参班,分别是:左翼头班为青海佑宁寺的章嘉呼图克图,左翼二班为青海广惠寺的敏珠尔呼图克图,右翼头班为青海塔尔寺的赛赤活佛(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右翼二班是西藏的济隆呼图克图,其余还有青海湟源县东科寺的东科尔活佛、青海塔尔寺的阿嘉活佛、青海塔尔寺的拉科活佛、青海佑宁寺的土观活佛、甘肃拉卜楞寺的贡唐活佛、甘肃拉卜楞寺的萨木察活佛,还有果蟒佛和鄂萨尔佛两位活佛的寺籍难以稽考。清政府所确定的12位驻京呼图克图,青海占了7位、甘肃占了2位,体现出清政府对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势力的重视,“有清一代,与清政府关系最亲密、受到宠信而常委以重要宗教事权的活佛,大多时期是章嘉、敏珠尔、赛赤、土观、阿嘉、东科尔等。”[40]197而清政府之所以大力扶持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上层,就是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宗教势力将对藏蒙地区的宗教管理权严格控制于中央,利用甘青而控厄西藏、蒙古。有清一代,清政府处理西藏事务,几乎都是把章嘉等驻京呼图克图作为最佳人选,派遣其赴西藏处理相关政教事务。西藏地方政府与清廷沟通,也基本是选派游学于拉萨的驻京呼图克图充任达赖喇嘛的信使,赴北京请旨听谕。而这些受到清政府恩宠的活佛,由于有政治势力的扶持,其寺院的地位也急剧抬升,对这些寺院在甘青地区的势力扩张,以及甘青地区的寺院兴衰分布都起到了重要影响。
四、交通路线的开辟对甘青藏传佛教的影响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与交通,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发展与传播也深受人口与交通的影响。“受高原多高山大川地势的影响,山口河谷是天然的交通线,而加上人口也多分布于河谷地带,连结各个居民点的交通线也必然是以山口、河谷地区为主。高原人口、交通多集中于南部、东部且呈线形分布的特点对于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41]171
历史时期甘青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是丝绸之路及其支线青海道以及连结西藏地区的唐蕃古道。这些交通路线的开辟,促进了甘青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迁徙与交流,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区域内的宏传与发展。
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早于西藏地区,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甘青地区成为中国最早受到佛教影响的区域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佛教在南亚大陆创立以后,不久就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中向北一路传至中亚各国,并越过葱岭进入中国西域地区。汉代打通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后,佛教又沿着丝绸之路逐渐向中国内地传播。《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42]3025西域佛教向东方传播扩散,最先受其影响的就是甘肃河西一带的居民。敦煌、凉州等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汉代以来即为西域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据《高僧传》记载,西域僧人东行传法常以此处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而长期居留。竺佛念、宝云、竺法护、法盛、智严、道普等初期著名的译经僧人都出生于这一带。当地居民对他们以礼相待,处之既久,也开始信奉佛法。可以说,与青海毗邻的甘肃河西一带是中国内陆最早受佛教传播和影响的地方之一。因此,顾颉刚先生称这里为“中印文化之媒介地”[43]365。丝绸之路青海道开通以后,也有大批僧侣经行此道或西行求法,或东来传经。法显、昙无竭、法献、宋云、阇那崛多等名僧都曾行经此道。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在甘青地区的早期传播也影响到了后来藏传佛教在这一区域的传播。吐蕃占领河湟陇右以及河西等地后,当地的一些民族和民众之所以能够接受藏传佛教,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早就根植了佛法的种子。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后,在和唐王朝的密切交往过程中整合区域内古老的交通路线形成了著名的唐蕃古道。这条路线也是伴随着吐蕃向甘青地区的军事扩张而形成的,是吐蕃各部族向甘青地区迁移的主要路线。在这种迁移过程中,甘青地区藏民族的分布格局逐渐固定下来,唐蕃古道沿线也就成为藏传佛教的重点传播区域。以青海玉树地区为例,“到1958年,全州共有藏传佛教寺院201座,分属噶举、萨迦、格鲁和宁玛四大教派”[44]860,是甘青地区寺院数量最多、教派最齐全的一个地方。推动玉树藏传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毗邻西藏,是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带。
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时,途经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巴塘乡西北约4公里处的贝纳沟南端,休整一月,公主命随行比丘译师智敏负责,由工匠仁泽、杰桑、华旦等在当地丹玛岩崖上雕刻出9尊佛像,中为大日如来,梵语谓“摩诃毗卢遮那”,藏语称“南巴囊则”;左右各侍立四尊菩萨,分上下两层,右上为普贤、金刚手,下为文殊、除盖障;左上为弥勒、虚空藏,下为地藏、观世音,共为八大近侍弟子像。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蕃再次联姻,金城公主入藏又经过玉树巴塘,见文成公主原刻佛像被风雨剥蚀,遂令随从于佛像上盖一殿堂。唐开元十八年(730),复派人摹刻佛像,修缮殿堂,并在殿门旁勒石立碑:为祝愿万民众生及赤德祖赞父子福安昌盛,依原刻佛像精雕,修盖此殿,此即玉树巴塘现存的大日如来佛堂,亦称“文成公主庙”,是青海最早的佛殿。[45]21-22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玉树由于在唐蕃古道中具有枢纽地位,在藏传佛教前弘期就有了佛教的传播。玉树也是吐蕃向青海扩张的第一站,是青海最早被吐蕃部众占领的地区。吐蕃占领这里以后,“玉树为吐蕃王朝东攻吐谷浑和唐朝疆土的军事重地,吐蕃派大臣坐镇玉树。这里为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和对唐发动战争提供兵源、马匹和其他军用给养,起过重要作用。因此,与甘青其他地区相比,这里与吐蕃本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公元11世纪后,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噶举、觉囊诸派相继形成,藏传佛教进入空前活跃时期,玉树地接卫藏、西康,加之原本联系密切和已有的古道,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再度弘传的重要基地。”[46]993
五、几点结论
(一)宗教是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传播都有其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基于这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其发展与传播也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于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发展的影响,需要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位地理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青海大部和甘肃甘南地区与西藏同属青藏高原,山水相连,自然环境相近,遂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流布地区。甘青两省其他地区,由于地缘关系,自然也成为藏传佛教传播的辐射地区。
(二)区域内的民族分布格局、信众基础等因素都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甘青地区是吐蕃王朝对外军事扩张的主要方向,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几乎占领了甘青全境,甘青地区遂成为藏族分布的一个重要地区,为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弘传奠定了坚实的信众基础。元明时期,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民族也开始在甘青地区错居杂处,藏传佛教也普遍传播于这些民族之中,成为这些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
(三)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体现出历代中央王朝对甘青地区的有效统治逐渐完善,也为这里多民族分布格局提供了制度基础。尤其元、明、清三朝对这里“因俗而治”,大力扶持藏传佛教以稳定这一多民族地区的政治形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四)甘青的地理区位使其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等交通路线的开辟,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甘青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迁徙与交流,也成为甘青地区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李悦铮.试论宗教与地理学[J].地理研究,1990(3):71-79.
[2]魏道儒主编,尕藏加著.世界佛教通史·中国藏传佛教(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
[3][11][41]王开队.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70;170;171.
[4]文忠祥.青海东部农业区气象灾害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1):47-50.
[5]杨仲华.西康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7.
[6][宋]王溥.唐会要·卷97[M].北京:中华书局,1955:1729.
[7]康敷镕.青海志·卷4[M].香港:成文出版社,1967:158-159.
[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72.
[9]李翌灼.西藏佛教略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室,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藏事论文选·宗教集(上).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5.
[10]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室,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藏事论文选·宗教集(上).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422.
[12]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40.
[13]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教源流[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245.
[14]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3.
[15]石硕.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J].西藏研究,1992(1):24-32+19.
[16]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5-6.
[17][39][40]白文固,杜常顺,丁柏峰,白雪梅.明清民国时期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社会[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204;147;197.
[18]周止礼.西藏社会经济研究蠡测[M].北京:北京财贸学院,1979:12.
[19]州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3.
[20]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1.
[21][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26.
[22]张生寅.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明清河湟土司与区域社会[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105.
[23][24][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127;128.
[25]许让神父著,费孝通、王同惠合译.甘肃土人的婚姻[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8.
[26]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载穹庐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11.
[27]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著.塔尔寺概况[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92.
[28]明英宗实录·卷50,正统四年正月乙巳[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29]明英宗实录·卷123,正统九年十月乙亥[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30]明英宗实录·卷124,正统九年十二月庚申[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31]唐景福,朱丽霞,牛宏.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J].西北民族研究,1999(2):248-259.
[32][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385.
[33]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565.
[34][民国]张其昀.夏河县志[J].方志,1935(9).
[35][45]蒲文成.青海佛教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24;21-22.
[36]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宗教志[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44.
[37]扎洛.藏传佛教文化圈[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4.[
38][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92:178.
[42][北齐]魏收.魏书·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25.
[43]顾颉刚.佛教下之西北[M]//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7:365.
[44]玉树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玉树州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860.
[46]蒲文成.古教遗珠光彩夺目:简论玉树地区藏传佛教的特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99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18XZS051)
作者简介:丁柏峰(1972-),男,汉族,天津蓟县人,历史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北区域史及历史地理学。
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3月第46卷第2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