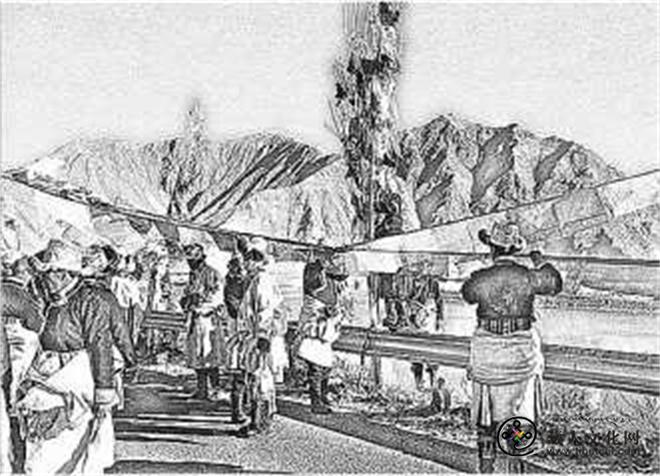——以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渔村为例
摘要:本文聚集于青藏高原传统的运载工具——牛皮船,提出“牛皮船文化”的概念,从物质、制度、精神方面进行多层次的研究,立体地透视文化与社会的互连关系,探究该文化能够在青藏高原得以存在的原因。全文立足于田野调查收集直观性的素材,并借鉴相关文献作比较,通过描述俊巴村民与牛皮船的互连关系来揭示藏族制作与使用牛皮船的方式,分析“牛皮船文化”的存在形态与存在依据,凸显文化的整体性,并寻求该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一江两河” 牛皮船 文化 俊巴村 互连关系 整体观
一、引言
“牛皮船”作为出行和运载工具在我国西南流域由来已久。吐蕃时期的牛皮船在桑耶寺壁画中可见,是圆形圆底船,容纳3-4人;周霭联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五十八年(1793)入藏记载“皮船以牛皮为之,中用柳条撑住,形如采菱之桶,仅容一二人。一番人荡(桨),其疾如飞。惟皮经水渍如败絮然,中流危坐,为之股栗渡毕则负归而曝之”;艾哈默德•辛哈于1894年入藏,曾依其旅行所见,手绘西藏渡船草图。上述文献将早期牛皮船的形貌、结构、承载量及使用方式做了记叙。现阶段,关于“牛皮船”的论述仅散见于新闻报道和文艺读本中,多从技艺或文学的角度对其分析,系统深入的研究较少。马林诺夫斯基曾将独木舟与岛民社会和库拉贸易圈紧密结合,在独木舟存在的社会系统中探讨船的特性;珍妮特·克罗夫顿·吉尔摩将渔船维修中11个渔民的生命史,船夫、渔民、维修匠人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融入其对俄勒同地区手工商业渔船的研究中;凌纯声、田汝康等探讨古船与东南亚渔业技艺、文化、航行和贸易间的关系,注重文化的传播与联系;塞格柏尔特·休麦和贵朵·沃廖迪指出西藏及长江、黄河上游的牛皮筏是古代近东和地中海文化向中亚迁移的证据,将皮筏置于全球文化交流传播的网络中。当代人类学研究极其关注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互连关系,正是在这一研究倾向的引导下,本文聚集于青藏高原的牛皮船这种物质生产及运载工具。
“牛皮船”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单纯性和复杂性。单纯性是指其作为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的物性与物效;复杂性是指以物为纽带所牵连出的一系列非物质的制度与文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田野观察和文献研究,提出“牛皮船文化”的概念来串联研究对象的互连关系,并以文化的整体观为指导,探索青藏高原此种文化存在的形态与原因。
西藏的牛皮船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区域(如图1)。大到“一江两河”中部流域(见图1中的小图)海拔3500米以上、幅员6.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含拉萨、日喀则和山南三个地级行政区,整个流域内牛皮船的使用较为普遍。除了大空间,还有小空间的含义,也就是本文田野调查点俊巴村。
俊巴民俗自然村隶属于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茶巴朗行政村,“俊”是捕手,“巴”是人的意思该村位于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北距拉萨60公里,西距拉萨河对岸的曲水县城3公里。村庙在西北方的曼达山马鞍形山腰处,村内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此举行。村东南面的白马拉错被誉为神湖,与村民捕捞有关的传说和此湖有紧密的联系,村中集会、跳牛皮船舞等活动在神湖西侧的草场举行。全村有98户,386人,男女比例为1.01:1,村民的主要构成是渔民和皮匠,基本生计是捕鱼、农耕、放牧和皮具制作。牛皮船集合了渔民和皮匠两种职业,聚合该村居民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可用人类学关于“文化”的定义来看待它,故称为“牛皮船文化”。
 图1:位于“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俊巴村布局
图1:位于“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俊巴村布局
俊巴村保留着完整的牛皮船文化,2004年之前,出行和捕捞的主要工具依然是牛皮船;2008年,该村的牛皮船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俊巴传统皮具制作技艺和鱼宴被列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于2015年2月、2015年7月至8月、2016年1月至2月、2016年6月至9月,分四次驻村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获得深切的感受。文中所用全部图表均为笔者自行拍摄绘制。
二、“牛皮船”与“俊巴捕捞传统”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西藏居民不打鱼、不食鱼,但存在于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村以捕捞为主要生计,以牛皮船为摆渡、捕捞工具,进而形成的“牛皮船文化”显然与常理相悖,这种相对边缘的文化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一)神湖与渔民祖先
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在史前文明就有早期渔猎。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中存在石质矛头和箭镞属狩猎工具。“在几座灰坑中还见到有鱼骨,当是曲贡人食用拉萨河无鳞鱼的证据,这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类似于曲贡遗址的文化遗存,在雅江中游河谷区的贡嘎县昌果沟和琼结县邦嘎村也有。贡嘎县昌果乡到俊巴村的距离仅为40公里,出俊巴村过嘎拉山隧道(见图1)往东一直走,大概15分钟车程。
俊巴村中流传着“神湖”与祖先“巴莱增巴”的传说,与八大藏戏中«诺桑王子»中的一段不谋而合。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在白玛神湖(俊巴村东南面的神湖,见图1)上以捕鱼为生的渔夫名叫“巴莱增巴”,当南部酋邦的首领派遣巫师攻打神湖下的龙宫时,渔夫勇斗巫师,解救龙王,被赐予了宝物。神湖属地的王子诺桑想娶仙女为妻,渔夫将龙王给其宝物换成能捆神仙的索帮王子得到了仙女。渔夫被王子赋予了捕鱼的权利。俊巴村一江之隔的茶巴朗村就有诺桑颇章遗址,传说为诺桑王子的宫殿,神湖亦属诺桑家族属地。渔民祖先“巴莱增巴”在此打鱼繁衍俊巴人也沿袭了古老的打鱼技艺。
但自西藏全境盛行佛教后,打鱼这种杀生行为与宗教相悖,渔民也被认为身份低贱而倍受歧视。村中又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藏王得知俊巴村民打鱼,派重兵围困水域,要饿死所有村民以祭祀神灵,俊巴陷入绝境。村里有位勇敢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祭拜过‘巴莱增巴’圣人后,只身来到拉萨河捕鱼。他从水中捕获貌美的姑娘并将其放生,姑娘感谢他,要和他一起去仙境生活,被拒绝了;他又拒绝了姑娘赠予的宝物。年轻人说需要鱼来救那些即将饿死的村民。姑娘知道俊巴村的处境,打扮得如新娘一般,告诉年轻人,你心灵纯洁,感动了圣人,把我送给藏王,你们还可以过上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年轻人照做,藏王高兴地应允俊巴村民世代打鱼、食鱼的请求,撤走了重兵。”
上述传说涵盖了俊巴村自西藏统一前的酋邦到王朝国家(吐蕃王朝)的历程,渔夫都被塑造成具有正义、勇敢、忠诚、善良、不贪财色等品质的英雄形象,其勇于牺牲、不畏艰险、正直善良的特质是与佛教文化相一致的。村民认为,祖先的英勇使后代获得了捕鱼、食鱼的特权,捕鱼是王赋予的权利。实质是在宗教与王权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以一套地方性的话语,使渔民捕鱼具备合法性。村民们通过传说凝结认同、寻求理解,亦是渔民摆脱佛教杀生罪孽与卑贱感的心理依托。勇于牺牲、不畏艰险、正直善良也成为村中进行道德评判的重要标准。
(二)税役与捕捞权
1959年以前,西藏属封建农奴制,土地、江河、物产都属于地方政府或寺庙,俊巴村系哲蚌寺属民,归协荣谿队罗塞林管辖。村民需支内差和外差,内差包括奴役性地租、劳役及人身依附费等,外差以政府认定占有或使用的土地面积(牲畜数量)为依据,征收实物(或货币)税赋及征派乌拉劳役。
渔民们每年要划牛皮船运送藏茶、羊毛、青稞等,承担西藏地方政府长途运输的外差。同时在政府户籍册里的渔民,“需在缴纳每年的鱼税后,从事捕鱼生计,按惯例,除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冬季或禁渔令时段的鱼税外,还需向宗府(曲水宗或贡嘎宗)和拉恰列空(噶厦管理税务的行政机构)缴纳鱼税。噶厦政府时期,渔民需缴纳的税差有近30项,包括“乌拉、皮具税、皮张税、糌粑税、柴薪税、鸡蛋差、饲草差、牲畜差、饲养马匹和厨房服务差、各种活动的卓巴差(跳舞人)、林木草场差、灯芯差等等。江河边耕地有限、水患频繁,单靠农耕所获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多赋税,每年辛苦耕种,收获的青稞80%要给领主交土地税,自己的20%根本不够一家吃一年。如果收成差或者遇灾害,交不了税的,就欠着,付高额利息,利滚利,债是如何也还不完的。
沉重的赋税使村民的生存难以维系,他们选择利用江河中的鱼类资源。同时,寺庙及地方政权的日常运行需要大量的上缴稅品和劳力,以“牛皮船”为工具的运输乌拉差对政府的物资流转极其重要,因此,除山水禁令颁布的特殊时期,地方宗谿一定程度上以鱼税和差役换捕捞权,默许村民的捕捞行为以维持地方统治,这也为“牛皮船文化”的存在换取了有限的空间。
(三)鱼农交换的客观需求
青藏高原物资匮乏,物物交换是换取资源的重要手段,而交换又依赖牛皮船出行,因此拥有和驾驶牛皮船也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皮子对俊巴村人也更为重要,冬季宰杀牦牛时亲戚、邻居赠予的湿皮,不需要费用,但必须以礼物或换工抵偿。干皮多从拉萨购得,皮从藏北运来拉萨售卖,都是冬季交易。20世纪40年代一张普通牦牛皮的价格在6-7元,大的要10元左右。干皮有时也去山南换,山南有藏北牧民过来换青稞,就以藏靴、糌粑袋、背囊、马鞍进行物物交换,干皮易于保存,就不用急着做船或皮具。牛皮船损坏后后的皮子可以用来做衣服和包,长时间在水中浸泡的皮子柔韧性好、耐磨,附近茶巴朗村山沟里的8组和9组的村民最喜欢过来买这样的衣服他们会用干皮板或干牛肉、糌粑、酥油等交换。
每到节日,村民还会去拉萨的八角街、布达拉宫和哲蚌寺、色拉寺附近贩卖皮具。很多僧人喜欢皮质的衣服御寒,买来揉好的皮子自己制作。曲水大桥等集市也是农牧民进行物物交换的重要场所。
渔民的鱼也是有市场的,虽然有些藏民不打鱼,但吃鱼。尤其是藏历5月,青稞还未收割、冬储的牛羊肉类亦吃完,能吃到鱼就是很大的满足了。以前,买卖的是死鱼,打完鱼去拉萨走街窜巷,不能说卖鱼,只能说卖“水萝卜”,有人就心领神会出来买。在拉萨卖鱼会有些现金收入。但去山南或曲水县、尼木县附近的农牧区就没有现金,换青稞、奶渣、盐、藏香之类。有时候农区青稞未成熟时,就没有青稞交换,可以赊账,待收获打谷后再收相应的青稞回来抵账。20世纪70至90年代,部队在拉萨有很多食堂,村里生产大队会去和食堂以鱼换生活用品。据报道人扎西顿珠介绍"“20世纪70年代,打鱼团队会和西藏驻军食堂以鱼换食品及生活用品,也有卖给藏药厂的,收入可观,钱物交回生产大队,统一分配。”那时候的压缩饼干、军大衣、军用罐头、军用油在城市也是稀罕物,但村民是能吃到、用到的,至今村中对部队的军需用品都格外喜欢,煮面都爱放军用罐头调味道。
村落间物物交换的需要为鱼农贸易提供了市场,为“牛皮船文化”的保存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本文受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人类学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奖助金” (项目编号: TYJZJ2015)、中山大学“2015年度中国田野调查基金.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科研支持计划” (项目编号:303029 - 20150210)资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何国强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特对何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对俊巴村民的无私 帮助和包容理解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张婧璞(1984 -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刊于《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